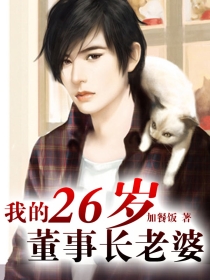4:15 S
“从十七岁开始说吧。”
拇指大小的周平指了指那漂浮在空中的绿军衣青年,因为那男孩手里拿着画笔,和中年画家手里的那支笔一样。
“十七岁么?”
中年画家揉了揉额头,他用手在空中一抹,哭泣的小婴儿和奔跑的小男孩像玻璃窗上的雾花一样模糊成水滴、然后汇聚在一起落入浴汤之中,只剩下那个拿着画笔的绿军衣青年。
再接着他又用画笔在绿军衣青年身旁画上场景,旋即漂浮在空中的人物和场景交融在一起,一帧一帧地开始动起来,就像是老旧的幻灯片一样。
“十七岁那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而这转折点之后我便一直在流浪中度过。”中年画家一边说一边在空气中画着,奇妙的是他说到哪里,空气中那如同老旧幻灯片似的画面就变到哪里,“那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十七岁的我刚上了大学,上的大学也不是什么名校,上的是一座沿海城市的艺术专科院校。”
中年画家又在空中画了一间又一间的画室。画完之后,绿军衣的青年一只手握着笔、一只手拿着调色盘,穿着被颜料染成五颜六色的白衬衫,眼神透亮地在画室之间不停地跑来跑去。
“刚进大学的我对一切都很好奇,几乎每个老师的课我都去蹭着听。美术专业的课程自然是不用说,其他专业的课程只要是我感兴趣的我也会去听一听。”中年画家在空中挥动着的画笔停了一下,转而杂乱地画了几个大叉,“不过平静的日子总是很短暂,大学刚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开始席卷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所有的学生都戴上了红袖套。打倒、革命、斗争,一时间耳边被这些字眼充斥了。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发了疯,不管是在学校里读书的,还是在工厂里上班的。唯独我依旧画着自己喜欢的画,对身边这些不可理喻、愚不可及的事情,充耳不闻。”
“不过我终究还是不能置身事外,随着这股反文化的风潮愈演愈烈,我喜欢的老师全被批斗了一遍,然后打包丢进‘牛棚’。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想看的书也都被列为违禁物,身边的人都被狂热的口号冲昏了头脑。于是在十八岁那年我申请了休学,准备回家。”
中年画家在空中画了一条又长又陡的路,然后那个绿军衣的青年便背着一个没有纽扣的单肩包上了路,
“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傻眼了——我家的门大开着,家里的东西被人搬了个精光,家里也没有一个人。
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当过兵的父亲被人举报了。
举报的人是我叔叔,举报的理由是说我父亲在彭德怀手下做警卫的时候有把手枪,在朝鲜战场回来复员的时候给带回了家。
结果我的家就被那些造反的人抄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但这还不算完,他们在没有搜到手枪也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就把我爸抓去劳改。我妈妈也不能幸免,被抓去上思想教育的学习班。而且造反派还发动我家的亲戚朋友去到处找我父亲私藏枪支的证据,说是发现有奖励。
知道了这些事后,我天天做噩梦,梦到自己被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围住,然后批斗来批斗去。他们对我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被他们捆住了手脚跪在地上,身上都是臭鸡蛋和烂菜叶。
所以在回到家住了一个月后,我又背上了那个没有纽扣的单肩包,然后独自一人地到处流浪。流浪到一个地方,就找一个不需要身份信息的体力工作做,空的时候就看看自己放在单肩包里的违禁图书,然后拿出笔和纸把这地方的景物画下来。一旦发现好像有自己从前认识的人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变马上离开这个地方,继续流浪……直到我三十岁那年的冬天流浪到一个小县城,遇到了一个女孩。”
"哦,女孩?"周平打断了中年画家的话,“怎么样的女孩?”
画家仔细地洗了下自己的画笔,然后试图画出他脑海中女孩的模样,可每次他画到一半的时候就忍不住把原先画好的线条全部擦掉。
“样子我想不太起来了,只记得她是一个小县城里浴场的勤杂工,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见到她之后,我便在这小县城里住下了。
那时的我以为自己是喜欢上了这个小县城,因为这里有冬天干完体力活后可以舒舒服服泡个热水澡的浴场。虽然那时候的我依旧是干着无趣的体力活,拿一点饿不死人的报酬,但是我有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然后在小县城里四处写生。
偶尔因为看书看入迷了,拿着一本当时的违禁图书一边走一边看,被路上的人看到了,他们也不会去深究什么、去举报我,只是说一句当地的土话笑话我——‘书糊’,然后从蛇皮袋或者是菜篮子里拿出一点新鲜的时蔬分给我。
我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回去浴场前的那条山涧里捉几条肉质肥厚的河鱼,然后配上时蔬吃。当然困难的时候,山上的野菜也是吃过的。
不过野草也好、河鱼也罢,那里食物的味道全都是我记忆中无法忘却的美味。
在我住在那里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之所以自己无法忘掉那里食物的味道,是因为那里与世隔绝,我可以在哪里尽情地沉湎于读书和思考,不用再去关心现实世界中那些毫无意义又复杂繁多的事情。
但后来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明白——之所以自己无法忘掉那里食物的味道,是因为我喜欢上了那个小县城里在浴场当勤杂工的女孩。”
“啊~呼~”周平听着中年画家讲这段四十年前的故事,觉得有点想睡觉,因为这段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对周平来说是完全没有经历过,更别说产生共鸣,“能不能把无关紧要的事情都省略掉,我就想听那个浴场女孩的故事。”
“这有点难,因为那个浴场里的女孩和我说的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都有联系。不过你嫌我讲的故事太慢的话,我可以挑些主要的给你讲。”中年画家把笔放在地上,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上那幅《最后的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