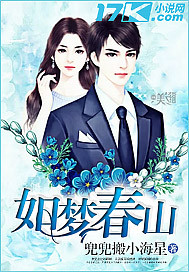夜沉如水,轻柔的晚风里夹带着雨后青草的芬芳,弯弯的一角新月,正垂挂在天上。
“姐姐,我想跟你说件事。”迎春枕着手肘,侧身躺在宋欢颜的身边,小声说道。
借着一盏昏黄澄莹的烛光,迎春只觉,她的脸颊温柔地就好似一朵含苞待放的睡莲,又长又密的睫毛不时微微颤动,像是停落在花尖上的蝶,仿佛只要轻轻呼口气,它就会展翅而飞。
宋欢颜轻轻地“嗯”了一声,她还没睡着,明明已觉疲乏,却是始终无法安睡,只能躺倒在床上闭目养神,静静地想些心事。
迎春闻言,伸手从枕边拿起簪子挽着披散的头发,掀开薄被,撑着身子坐起来。
宋欢颜感觉到她在动来动去,睁开眼睛瞧了一眼,轻声道:“嗯?你怎么还坐起来了?”
迎春闻言,又笑嘻嘻地看向宋欢颜,只道:“姐姐你看,有人托我带个东西给你。”说完,她又从枕下拿出一只小小的绣花荷包,放在宋欢颜伏在腹部的手背上。
宋欢颜略有些迷茫的拿起看了看,问道:“谁给的?”
迎春笑得很愉悦:“是表少爷的给的。晚饭过后,他去厨房叫我,让我把这个捎给你。”
宋欢颜闻言,立马觉得手中握着的荷包变成了一个极为烫手的山芋,连想都没想,就下意识地将它扔到了床上。“胡闹!明天早上把它还回去!”说完,有些赌气似地背过身去,继续道:“迎春,以后,别再做这样无聊的事了。”
迎春见她这般,神情微征,伸手轻拉了一下她的衣服,道:“姐姐,你生气了?”
宋欢颜道:“我没生气,只是有点心烦。”一会儿是画一会儿又是荷包,自己这个表哥还真打算继续折腾下去不成?
迎春捡起床上的荷包,放在自己的手掌心里,细细打量一番,好一会后,才压低声音道:“姐姐,其实表少爷对你挺上心的...”
宋欢颜皱皱眉头,只作未闻,望着床边轻薄的蚊帐没说话。
迎春盯着她的后背,轻咬了咬下唇,接着道:“表少爷这人虽然脾气急了点,但心肠并不坏,而且,也不是外人...”
宋欢颜听了这话,心里更烦,翻身看了迎春一眼,疑惑道:“迎春,你今天是怎么了,好端端的说这些作甚?难不成,我表哥让你过来给他当说客了?”
迎春闻言,连忙摆摆手道:“没有没有,表少爷没让我说这些,是我自己多嘴多舌...”
宋欢颜几乎没有表情的坐起身来,见她脸上的神色有些失落,轻叹一声道:“我对表哥他没有心思,往后,他再托你做这样的事,你一定要拒绝掉。”
迎春低着头,用食指尖一直摩挲着荷包上的绣花图案,似乎有几分惆怅的样子。“我知道了。”
宋欢颜见她垂头丧气的,便伸手推了推她道:“天晚了,快睡吧。”
俩人重新躺回到床上,肩并着肩平躺着,好半天都没说话。须臾,宋欢颜望着床顶,缓缓道:“此生身为女儿家,我已经失去很多自由了。嫁夫择婿,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我想自己做主。”
迎春闻言,翻身面朝着她,吞吞吐吐地开口问道:“那姐姐..准备自己找夫婿啊?”
“依我这个年纪,说这事还为时尚早,一切还是看缘分吧。”人生有些事是强求不来的。
迎春说:“姐姐也不能不急,女孩家一到了十五岁就该订亲事了。”
宋欢颜淡淡道:“我不在乎那些,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我没道理要委屈自己去遵从别人的目光。”
迎春作为封建保守的古代女子,自然无法体会宋欢颜的那份自由超脱的心境,只隐隐觉得她说的话,虽然新鲜大胆,却也很有道理。不过,这样大胆新潮的想法,只有她能想得到,也只有她能做得到。
迎春轻轻地点点头道:“嗯,姐姐说的对。我相信,姐姐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的。”
宋欢颜闻言,看向她,笑了笑道:“我看呐,还是先给你找一个吧。”
迎春一时间还有点反映不过来,随后微红着脸道:“姐姐你又笑话我了。”
宋欢颜伸指在她的额头上一戳,含笑道:“谁让你先起的头。”说完,她又将手收了回来,打了个哈欠道:“不闹了,我这会可真要睡了。”
迎春顺着她的话答应了一声,跟着帮她盖好薄被,翻身面朝床内躺好。待听见宋欢颜发出轻浅规律的呼吸声之后,她才悄悄地翻了个身,把一直握在手里的荷包,偷偷地举起来看。
这荷包小巧玲珑,越看越觉得有趣,渐渐地,迎春的心思从荷包飘到了它的主人身上。虽说,表少爷这人不易相处,又身有不便,但总算是生得清秀,特别是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边会浮出两个小小的酒窝,看着还是挺讨人喜欢的。想着想着,身边的宋欢颜突然翻了个身,吓了她一跳,耳朵跟着就烧了起来,自己觉得有些羞,有些尴尬,连忙将荷包收起来,闭上眼睛,不敢再胡思乱想了。
第二天一早,迎春按着宋欢颜的嘱咐,把荷包给何福官送了回去。
何福官听了,脸色晦暗,明显有些不大高兴。
迎春垂目不语,将那荷包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便转身离去。谁知,她刚出房门,就见那荷包被他从窗户扔了出去,落在地上。
迎春咬了咬下唇,不知道该怎么办,犹豫片刻,方才走了过去将荷包捡起来,拍了拍土,收在自己的袖兜里。
宋欢颜坐在窗前看书,正巧将这一幕看进了眼里,看着迎春那张红彤彤的小脸,眼神中闪过几分无奈....
待三伏天一过,早晚的天气变得稍微凉快了些,只有,正午时分的太阳依旧是热辣辣地灼人。
田氏之前说的三个月禁足令,没能执行彻底。还不到半个月的工夫,田氏就因为经不住孙女的软磨硬泡而缓和了态度。不过,老人家对上次的事依然心有余悸,所以把禁足令改成了限时令,规定宋欢颜每天酉时之前必须回家。
保和堂和芬芳小店摊满了大大小小的事,宋欢颜只得两头跑,从早上一直折腾到下午,直到田氏派来迎春过来叫她,她才得空喝了一口茶。
迎春是一路跑着过来的,宋欢颜看见她气喘吁吁的模样,微微纳闷道:“干嘛慌慌张张的?”
迎春说:“姑娘,你快回去一趟吧。表少爷闹得太凶了,家里没人能劝得住他。”
宋欢颜闻言,想着他那不利落的腿脚,遂起身往家走去。
谁知,还未来得及进院门,就听一声极其清脆的声响落在门口附近。宋欢颜本能地停了下来,寻思着准是何福官又砸东西发脾气呢。
迎春抢先一步推开院门,只见,屋里摔东西的人并不是何福官,而是显了身孕的胡氏。
她拿起桌上的瓷杯就往地上砸,口中还念念有词道:“砸,今儿咱们娘俩儿索性就砸个痛快!砸,我陪你一起砸!”
宋欢颜提了裙子抬脚跑进屋中,劝阻道:“大家都住手!”
胡氏见了宋欢颜,也不说话,只用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眼神中带着一丝探究的目光,好像是想从她的脸上找出什么问题的答案。
宋欢颜看着满地狼藉,不由开口问道:“舅母,你们这是怎么了?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
胡氏看着她,心中滋味甚是复杂,张了张口,却没说话。此时,何福官瘫坐在扶手木椅上,垂拉着脑袋,满身地酒气,待见宋欢颜进屋之后,便拄着桌角直直站起来,定定地看着她,正欲张口说话,却被胡氏制止道:“红菱赶紧扶少爷下去歇着,他喝醉了。”
红菱默默地点点头,踩着地上没碎片的空隙,正要伸手去扶他。却被何福官接着酒劲给推了回去,险些让她摔倒在地上。
宋欢颜见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幸亏,红菱自己及时站稳了,要不然倒在这满是碎片的地上,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何福官看向宋欢颜,一步一挪的走到她的跟前,长长地吐了一口酒气,幽幽道:“原来你已经攀上了沈四九,怪不得……你平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宋欢颜先愣了一下,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沈四九?你这话什么意思?”
何福官扯了扯嘴角,冷笑一声:“你别不承认了,城中早都传开了。”沈四九痛扁刘威,为的就是保和堂的那位小娘子。
宋欢颜闻言,扫视了一圈大厅,满脸困惑道:“你们把话说清楚。”你一言,他一言的,到现在她也没弄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儿?
胡氏有些忍不住了,肃着脸道:“颜儿,舅母知道,凭着沈家的条件福官他比不过,也不能比。这一切都是你的福分,舅母不拦你。可是,你既然心里已经有了人,就不该瞒着我们,害得福官..唉...让我们全都稀里糊涂地蒙在鼓里。”说完这话,她一连叹了好几声,听着似乎是在埋怨宋欢颜,又似乎是在埋怨自己。
什么乱七八糟的?宋欢颜觉得郁闷之极,有些恼,侧身坐到旁边的椅子上,重重地捶了桌子一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