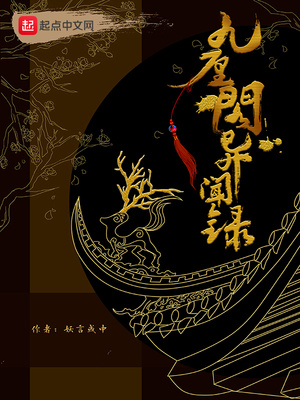屋后众人各自无语,慕容则紧紧拉扯着哥舒翰,以防他直接冲进屋里把这母子俩暴打一顿,五人暂时按下怒火,悄悄从院中翻墙而出,却见王忠嗣和皇甫惟明也是脸有怒容。方才杜氏声音如此尖利,他们站在院外竟然听得清楚。
五人快步向北出了坊墙,转进康俗坊内,走到一处荒僻无人的小茶亭坐着,个个憋了一肚子火,倒比李延青本人还要气得厉害。
这些日子众人在洛阳自在逍遥,全赖李延青纵容款待,便在朝中为官,也是或多或少处于他的荫蔽之下,才能如此顺风顺水。
再加上他为人雅量高致,器范超然,有大才而不外露,居高位能服下僚,深得众人之心,就连哥舒翰鲜少瞧得起人,也是对他心悦诚服,甘受驱策。
怎奈狄仁杰对李元芳一家恩重如山,李延青对狄家简直是有求必应,此番明皇赏赐钱物,大半都花在了狄博逊身上,生怕自己照顾不周,有负狄公之恩。
如今杜氏将这恩情当做软肋拿捏在手,就算真要李延青削骨割肉,只怕他也得乖乖照做。还真是无可奈何。
默坐一刻,哥舒翰终于一拍大腿,暴喝道:“不成!管他是谁的儿子孙子!我得先去打那小子一顿,不然这就要死!”
慕容则慌忙按住他道:“哥舒兄着什么急!”
哥舒翰轮睛鼓眼道:“如何不急?狗头鼠辈!也敢这等放肆!李将军是甚么人,晌午不知受了多大的委屈!若由着他们作践,哥舒翰在洛阳没脸混了!”
王询在旁道:“怎么打?我帮你!虽说老子不打女人,那个烂嘴老妇怎么也给他一并算上!”
张拯和源弼在旁点头附和,王忠嗣默然不语,皇甫惟明道:“诸位息怒。再是愤懑,也得顾及李将军。若他知道咱们将他舅母表兄痛打一顿,只怕也不高兴。”
慕容则点头道:“允辉兄说的不错!要打也不能自己动手,多得是法子。”
哥舒翰这才怒气稍歇,慢慢坐好。
张拯嗤了一声,道:“真不知狄大哥,在并州过得甚么日子。母亲弟弟竟是这幅德行。好歹是狄公亲孙,说出去不怕堕了先人的英名?”
源弼接道:“我倒是听闻,这个杜夫人原是婢女出身,当年狄公曾因这门婚事大发雷霆。”
哥舒翰道:“这怎么说?”
源弼道:“我也是听长辈提及,狄公曾说‘家无贤妻,岂有贵子,娶妇不贤,破家之祸。’因此要家中子弟须娶贤淑妇人为妻。谁知狄景晖非要娶这位杜夫人为正室,狄公一怒之下,险些将狄景晖逐出家门。如今看来,狄公远见,当真教人佩服。”
狄博逊虽然人品尚可,才能却稍显平庸,狄博逸更是狂妄无知,是非不明,这等后人如何振兴门楣?能一生平安都是天赐之福了。
众人秘密细谈一回,浩浩荡荡回到尚贤坊,果见狄博逊双眼通红,灰心丧气地坐在堂上,见他们回来,仍是提起精神,赔笑寒暄。
李延青道:“你们去了何处?”
慕
容则笑道:“忠嗣说他在燕然山射下的那只金雕,如今驯养熟惯,邀我们前去观赏一番。果然不错!”
王忠嗣漠然瞧了他一眼,若论信口扯谎,只怕谁在慕容则这里都要甘拜下风。
众人闲聊,绝口不提狄博逊家中探亲之事,狄博逊噎着满心苦涩,神游天外。
如今李延青身边众人,或家世显赫,如张拯源弼之流;或能力出众,如皇甫惟明,哥舒翰之类;再或是慕容则、王忠嗣这般出身显赫,又本领超群之人,才能和他共享高官厚禄。
自己家道衰落,才能平庸,只不过因为是狄仁杰亲孙,凭借李延青提携,才得和众人相与一处,想要融入其中,本已十分艰难尴尬。谁知又遇上一个惹是生非,悖傲自大的弟弟,和一个目光短浅,自私小器的娘,当真教人伤神。
只怕得是祖宗保佑,菩萨开眼,自己方能把这从六品的大理司直平安做下去。
不出所料,狄博逊刚到大理寺入职,诸般公事,同僚上司,都需一一熟悉,又怕母亲弟弟寻衅闹事,看管甚严,直忙得焦头烂额,接连数日不到尚贤坊去。谁知没过几天,又见他欢天喜地前来,与众人一道参加上巳节拔褉聚会。
原来杜夫人忽然一声不响地赶回了并州,匆匆来去,无人知晓。狄博逸虽然留在东都,奈何人生地疏,又没了母亲撑腰,竟也受到兄长管束,老老实实躲在府中,不提他事。
狄博逊如释重负,连说祖宗保佑,菩萨开眼。李延青在旁听罢,便知此事蹊跷。
杜夫人既有打算,所谋未成,怎么肯如此轻易地返回并州?环视身畔众人,目光到处,尽是躲躲闪闪,暗藏得意。
待狄博逊去拿太原美酒,慕容则大方干脆道:“是我们几个,不必你问,我直接招了。”
李延青哭笑不得:“你倒坦然。”
慕容则道:“左右瞒不住你。咱们兄弟连杨洄在内个个有份,你待如何?”
李延青朝王忠嗣看了一眼,见他也点头承认,一时无言以对。
慕容则哼了一声,又道:“难道李将军想让众兄弟给人活活气死么?万一忍不住动起手来,大家谁都不好看。这样处置,已是顾及狄大哥的颜面了,你还有甚么不满意?”
这话倒是不假。杜氏仗着自己身为长辈,耍横撒泼,李延青和狄博逊都对她无可奈何,但狄博逸多少心有畏惧,若无母亲撑腰,绝不敢随意放肆。倘若把他一并送回老家,狄博逊到底脸上无光,如此一去一留,除了杜氏本人之外,可谓皆大欢喜。
哥舒翰道:“将军若说此事办错了,哥舒翰把头摘下来给你。”
皇甫惟明和张拯、源弼乃至杨洄,都跟着齐声附和:“我也一样!”
王忠嗣道:“只要狄博逸安分一些,我担保无人跟他为难。”
王询幽幽道:“要不……我也做个担保?”
李延青听到这里,还有何话可说,摇头苦笑之余,心中也对众人关怀之意生出丝丝感激。倘若不是真诚相待,谁会管你受甚
么委屈?这些兄弟能为他如此,也着实不枉结交一场了。
杨洄先前深怕他出言责怪,一直忐忑不安,待见李延青神色渐转平和,这才放下心来,暗道:“我也多虑!上回公主之事,将军都不曾对我发难,为一点小事就如此揣测,我未免将他气量瞧得忒小了些。”
转念又想:“不知那日我喝得烂醉,给公主瞧见没有?她回到宫里,如今怎样?我安排大伙在此相聚,可惜她不能前来。”眼前浮现那双抱着兔子的纤白小手,恍若有甚么东西在心底搔了一搔,忍不住脸红面热。
去年李延青在曲江被明皇召入宫中,就此官运亨通,连带慕容则与张拯等人也纷纷入仕,前途可期,那场酒会因此传为佳话,惹来不少文人士子争相效仿。
比起长安曲江,东都另有风景绝佳之地,乃是洛河南岸,道术坊内一处百顷大湖,因曾被太宗皇帝李世民赐予爱子李泰,得名魏王池。
湖光清滟,新柳半染,舟鳞如鲫,行障似云,着实是个踏青的好去处。
池水西岸是长宁公主山池院,杨洄早就征得母亲同意,命家人选了一处临湖小楼,以供众人行乐游赏。
狄博逊那厢取酒归来,仆役接过送至楼上,忙着排布杯盘碗盏,众人先在湖畔闲步等候。
长宁公主这处池馆为昔日中宗李显所赐,彼时韦后正当得势,公主因有母宠,区区别苑也占了惠训、道术各半坊之地。堆山引渠,亭台林立,更将山中各样奇花、巨树整株移来,栽种其间,着实耗费钱财人力。
狄博逊伸手扶上一棵碾盘粗细的古松,正感叹皇家豪奢靡费,转头一望,远处梨、桃、李、杏、木兰、海棠各色花树,连结成片,芳菲正艳,粉雾如云。
树下另有芍药、蔷薇、绣球,棠棣,红云紫雾,一片阳春,看得人心摇神驰。怎奈万般颜色,都被一道修长身影生生压下了风姿。
慕容则静立花间,似在冥想。玉带凝光,襟袖迎风,鬓染青靛,容色皎然,任由落英簌簌,零洒满身,直教人想起月生沧海,孤清绝照的不染景象。
狄博逊一时看怔,恍惚回神,就听皇甫惟明感叹道:“‘有匪君子,如圭如璧。’所谓‘遗世独立’,也不过如此罢。”
张拯和源弼一面点头附和,一面感叹道:“那是自然!豫国府慕容家,莫说丑人,三代以内都找不出个相貌平平的来。”
哥舒翰调笑道:“我曾想泽川若是女子,该有何等绝色。如今看来,便做男子,啧啧……竟也如此标致。真不知以后,甚么样的姑娘嫁他为妻?”
他尚不曾见过宁安郡主,其余诸人却都想起上元之夜,慕容则百口莫辩,被迫跳河的一番遭遇,忍不住齐齐打了个寒战。这李唐皇族的公主固然不能招惹,郡主也是万万惹不得的。
分花拂柳,沿湖玩赏一回,仆役报说收拾停当,这就开席,众人一道登楼,顿时视野开阔,风物满眼,波光生艳,柳漾轻黄,教人襟怀大畅。
张拯道:“如何?今年还行不行酒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