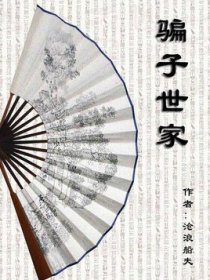第二天晌午,船到了北京码头,叫了三两辆马车,把货装好,一行四人就进了城。找了一家布行,讨了个合适的价钱,把一车上好的绸缎出了手。收好银子,在东直门附近,寻了一家客栈,开了两间客房,暂时安顿下来。
以后的几天,甄永信带着几个人在京城里转悠。京城是天子的脚下,冠盖如云,甄永信身着五品官服,在街上就显不出大小,几天下来,吃遍了京城风味,也把北京城大概摸了个差不离儿。
在客栈里住着,行动多有不便,又过了几天,几个人在王府井西街,租了一座临街的庭院。院落不甚大,前脸是京城四合院的布局,二进后面,是一幢小楼,院落稍显破败,前庭的墙壁上,长满了苔藓。好在租金便宜,往东又紧挨着参行一条街,平日里也算繁华。
甄永信吩咐顺子,到菜市场找了几个做苦力的,用了一天的工夫,就把院子里的杂草铲除干净,第二天又找来了几个装裱匠,买了些华丽的彩纸,没用两天,厅堂里就裱糊一新,有官宦人家的模样;又找来一个木匠,把后楼的地板做了些改造,说是为了方便到楼上取东西。只是从天津带来的妹妹,心有不甘,说跟着哥哥这等贵人出来,住着用印花高丽纸充当围帐的房子,真还不如天津卫的窑子里阔气。甄永信只好哄着妹妹,说这只是眼下暂住的,等往后自己买下房子,再用上好的丝绸当围帐。
随后的几天,他们又租来了几件像样的桌椅,陈设在客厅里;甄永信吩咐大宝、顺子,花极便宜的一点钱,在当铺里买回一些破箱子,码放到楼上的库房里;随后又雇来了门子和两个听使唤的小厮。
大约一周过后,这家大门口就变得热闹了,往来皆冠盖,出入无白丁。五品装束的主人,每日里不停地在大门口迎来送往,十天过后,两旁街市上都知道了,说这房子里住的,是济南府盐政使,届满回京候补,而这位候补官员的姐夫,则是现任两广总督大人。这种繁忙的应酬,一直持续了十多天,门前的车马,才渐渐稀落下来,候补官员才得空儿到街上走走,不时向街坊打听,这里哪家参行的山参地道,也时时看见他和几个酒肉朋友,喝得大醉而归。
大约又过了十几天,一天傍晚,顺子醉熏熏地从外边回来,手里还带了份《京报》。甄永信接过看时,赫然看见日俄战争的消息。半个月前,老毛子和小鼻子,在家乡金宁府血拼了一场,老毛子投降了,把半岛南端让给了日本人。看完《京报》,甄永信心里高兴,涌起一股战胜者的感觉。倒不是他心里喜欢小鼻子,而是因为他可以安心地回家了。离家多年后,第一次体验到了浓浓的思乡情,他又闻到家乡古城的上空,每天清晨飘散的炸油条的浓香;掠过城西的稻田,无风的日子,会传来海涛拍岸的声音;悠然飞翔的海鸥哨音,往往会和着涛声一道,划过古城的上空;即使玻璃花儿眼妻子,在乡思里,也变得不再那么凶悍可怖,眼上的玻璃花儿,也比实际轻淡了许多;老丈人和丈母娘,也都有了令人怀恋的长处,而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两个年幼的儿子,在他们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却那么无奈地离开了。京城虽云美,不如早还乡。这一夜,他打定了主意,把原定离开京城的时间,向前提前了几天。
早晨起来,甄永信把该干的事,向大宝、顺子交代完后,就叫妹妹把贵重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搬家。
“穷折腾啥呀?”妹妹怏怏不乐地埋怨道,“原本想跟着你过几天清闲日子,这可倒好,一天到晚的做贼似的。”
“最后一次了,下不为例。”甄永信陪着笑,哄着妹妹。
当大宝和顺子办完事,从外面回来后,甄永信就又带他俩出去了,径直来到福庆堂参行。福庆堂掌柜的,接财神一样,把客人迎进大厅,毕恭毕敬地给客人让了座,吩咐伙计看茶,干笑着说些客套话,在一边陪着。
“日前买了几家的参,回去比照一下,觉得还是贵行的地道。”甄永信品了一口茶,一手把着杯盖,在杯上轻轻刮着,一边对掌柜的说。
参行掌柜的听过,高兴得肚脐眼儿差点儿乐出声来,一向伶巧的口舌,倏忽笨拙起来,蠕动着不会说话了,只是咧着嘴,在一旁干笑着。
甄永信接着说,“昨天接到家姐丈的电报,说家慈已经在广州上了船,好歹就这一两日到家,我得赶紧把参准备好了。”
参行掌柜的听了,仍那么干笑着在一旁点头。
“这样吧,”甄永信接着说道,“这回我先少进点,你先照五千两银子的量,给我拣些六品以上的老山参,现在就带走。”
掌柜的领命而行,吩咐伙计从柜里拣参,亲自逐棵察看,生怕出一点纰漏。看看一切准备熨帖,甄永信又和掌柜的商量,“能否派两个伙计帮忙送过去?顺便把银子带回来。”
“敢情!”掌柜的立时指派两个伙计,去办这事儿。
甄永信说了声告辞,带着大宝顺子和参行的伙计,抬着一箱老山参出了门。
进了院子,大宝在前面引路,直把两个送货的伙计,领到楼上,开了库房的门锁,推门进去,甄永信随后跟了进来。这间库房,空间挺大,几大排箱子,整齐地码放在地上,甄永信指了指第三排第五口箱子,让大宝把箱锁打开,叫参行的两个伙计,把山参小心翼翼地摆放进箱子,装好后,把箱子盖好,上了锁,又让大宝打开紧挨着的第六口箱子的锁头,刚把箱子盖打开,一道白光从里面射出,定睛看时,是排列整齐的大锭银子。甄永信指了指参行伙计刚才送货用的箱子,问道,“就装进这口箱子里?”
“成!成!”两个伙计同时点头说道。
甄永信吩咐大宝开始秤银。大宝刚把秤具调好,忽听窗外楼下有人大叫,“玉成兄!玉成兄!在家干什么哪?今天是太原府知府坐东,你又打算逃席,是不?”
听闻叫喊声,甄永信急转身到窗前,向楼下看了一眼,马上旋了回来,脸色稍显紧张,赶忙吩咐大宝,把装银子的箱子重新锁好,回头对两个参行伙计说,“此人是我官场上的一个结交,最是无赖,先前多次向我告贷,却又屡屡不还,前日又要告贷,我以手头无银为由,回绝了他,今番要是让他上楼撞见这些银子,势必伤了和气。这样吧,先委屈二位,在这库房里稍待片刻,我去把他应付走,马上就回来。”
两个伙计根本没有说话的份儿,甄永信吩咐大宝先把装银的箱子锁上,就和大宝出了库房,又嘱咐大宝把库房门上了锁,而后下楼去应付在楼下说话的人。
甄永信到了院子,院中的来客,说话声音越发高起,不住地责怪他,生拉硬拽,把甄永信弄出大院。甄永信前脚刚出大门,在院中干杂活儿的两个小斯,就搬起口舌,声音越吵越大,脏话不绝,一会工夫,索性扭打起来。被锁在楼上的两个参行伙计,听着有趣,聚拢在窗边,拿手指捅破窗纸,往外看起热闹。
到了街上,甄永信给刚才进院吵闹那人一两银子,嘱咐他到东来顺叫一桌好菜,说等他忙完了家里的事儿,随后就过去。说罢,见那人接了银子走远了,甄永信转身从墙外东边的胡同折到后门。这时,大宝和顺子已把预先雇来的马车装好,甄永信跳上车,给了顺子一锭四十两的银子,叫他赶快坐黄包车到码头上,订一只去天津的快船。自己却坐着马车,带上大宝和妹妹,奔东直门,往城外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