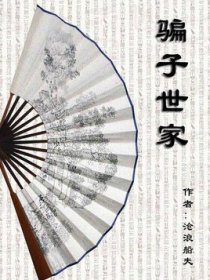甄永信进城的时候,天已傍晚。从东门进来,向北拐,就到了岳父家的门口,跳下车就和车夫往家里搬行李。玻璃花儿眼先是一愣,随后就叫出声来:“天呀,你个瞎鬼,这些年死哪儿去了,你?”说着,拿拳头捶丈夫的肩膀和前胸。
甄永信知道,这种捶打是喜极而为,和早先扇耳掴子不一样,心里也就不害怕,只是轻轻推开,“别闹,别闹。”一边给车夫付了钱。眼看马车离去,才赶紧把门栓上,叫玻璃花儿眼帮着把箱子搬到炕上。
“啥东西哟,死沉死沉的。”玻璃花儿眼嘴上抱怨,心里偷着高兴,想这箱子里装的,绝不会是石头,至少也应是值钱的东西,要不丈夫眼里怎么那么兴奋?尽管已有心理准备,当丈夫把箱锁打开,掀开箱盖时,玻璃花儿眼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妈呀”一声,跌坐到地上。“哪弄的?”她指着箱子里白晃晃的东西问道。
“赚来的呗。”丈夫得意地说。
老丈人和丈母娘几乎是在女儿惊叫的同时,闯进闺女房间。在这之前,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一整套尖酸刻薄难听的脏话,打算在短时间内,灌进窝囊废女婿的耳朵里,只是当看见箱子里放出的白光时,两眼就被晃得睁不开了。甄永信及时地从箱子里取出两锭四十两的银子,递给老丈人,岳丈攥紧了银子,生怕掉到地上,推说,“不要、不要,自家人还用这样?”
“这些年小婿在外闯荡,一家人全靠老泰山照应,岂是两锭银子所能报答的?好在来日方长,还有报答的机会。”甄永信伸出两手,挡住老丈人,一边劝老丈人把银子收下,嘴上一边客气道。
“哎哟哟,姑爷子见外了不是?”丈母娘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往日好听了许多,眼神也变得慈祥可亲,说话时,甚至还露出她这种年岁的人不该有的羞答答,“一家人,说这些话,也不怕外人见笑。”
两个儿子从大人腿下挤到前面,两眼直盯着父亲,老大世义八岁了,已开始穿死裆裤,还认得爹,玻璃花儿眼鼓动着他赶快叫爹,他反倒把嘴唇咬得紧紧,一声不吭,眼里噙着泪水;老二世德六岁了,还穿开裆裤,母亲刚让哥哥叫“爹”时,他就抢着叫了声“爹!”甄永信把老二抱在怀里,拿脸使劲儿贴着儿子的脸。
“你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玻璃花儿眼急着想知道丈夫这些年的阅历。
甄永信本想展样一下,说去当官了,无奈昨天晚上,在复州城大车店里,由于担心穿大清的官服,从岗子的哨卡入关时,会遇上麻烦,就把官服扔掉了,换了一身缎子马褂。这样,他只好说是去跑生意了。妻子问他做什么生意,他说什么都做过,贩卖药材,绸缎,人参,种种不一。妻子问他都到过哪些地方,他只说了几个大都市,奉天、天津、北京都去过。
老丈人听得直流口水,手里一直握着银子,不迭声地赞叹,还转过头对老伴说,“看见了吧,我就早就说过,咱姑爷不是个简单的人儿,只要闯出去,准是一条龙。”
唠了一会闲嗑儿,玻璃花眼忽然想起了什么,就跑到厨房,从锅里端出饭菜,又重新加做了几个菜,丈母娘也乐得直流口水,坐到灶下,帮女儿烧火。
从这会儿开始,甄永信和岳父才有了共同语言,老丈人又开始讲他早先任松江团练副使时,和胡子打交道的那些传奇,直讲到女儿把饭菜摆致到桌上,老丈人就停下话头,盘坐在炕头,左手紧捂着揣在怀里的银子,只拿右手亲自给女婿夹菜。直吃到二更已过,甄永信才放下酒杯,和妻子回到自己房间,夫妻俩几经商量,最后把几个大箱子藏到了最安全的地方,才上炕睡下。玻璃花儿眼久旱逢甘霖,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主动干练,把回家的丈夫,狠狠折腾了一番,夫妻俩才筋疲力尽地睡下。
过度倦乏,再加上酒劲儿,再加上心里踏实,这一夜,甄永信睡得沉实,第二天直到太阳已上三竿,才醒过乏来,简单洗漱,吃了点东西,就出了家门。
家乡确实脱离了大清国,督统衙门上空,飘着白底红圆心儿的日本旗,街上偶尔有人穿着木屐嘎嘎走过,嘴里哇里哇啦,说着鸭子叫一样的东洋话。
从督统衙门东边的胡同向后街拐去,就是早先的甄家大院了,贴着临街的门房走过,甄永信拿手摸着门房的墙壁,心里百感杂陈,门洞下的大门关着,大门已经重新漆过,朱红色扎眼难受,甄永信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在大门口徘徊了一会儿,拿不准是不是要上前去敲门。停了一会儿,他掉头离开,径直往南街济世堂药房那边走去。
济世堂的生意还像从前那么好,坐诊的大夫,在给病人把脉、问诊、开方;柜上的伙计忙得陀螺一样乱转,不停地拉开药柜的抽屉,按方配药。瞅准一个机会,甄永信向一个伙计打听邵掌柜的在哪儿,伙计一边包药,一边冷眼看了他一眼,硬生生地说在后边账房里。甄永信推门进来时,邵掌柜刚刚喝完一杯茶,提起茶壶,准备倒第二杯,看见甄永信进来,他愣了一下,停止倒茶,茶具悬在半空,拿右手推了推玳瑁眼镜,完全没注意到甄永信是穿着缎子马褂来的,却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轻淡地问了一句,“有事吗?”
“有。”甄永信说,不卑不亢,坐到离邵掌柜不远的一把椅子上。
“什么事?”邵掌柜不屑地问。
“想和邵掌柜谈谈房子的事。”
“房子?”邵掌声柜警觉起来,脸色变冷,又推了一下玳瑁眼镜,“你不是早就卖给我了吗?”
“不错,”甄永信向前探了探身,“现在我想把它再买回来。”
“买回来?”邵掌柜把茶壶放下,闭上眼睛,搓了搓手,又睁开眼问道,“怎么个买法?”
“邵掌柜开个价。”甄永信扬起下巴,丝毫不肯示弱。
邵掌柜再次把眼睛闭上,又搓了搓手。这回闭眼的时间略长一点,睁开眼后,盯着甄永信说,“甄先生,这房子当初,可是你找上门卖给我的,不是抵押给我的。”
甄永信点点头。
邵掌柜接着说,“既然这样,现在你想买,咱就得随行就市,照市价走。”
甄永信点点头。
邵掌柜接着说,“那就请甄先生出个价吧。”
甄永信笑了,摇摇头,说道,“卖房子时,定价权在我这儿;现在我要买房子,定价权在邵先生手上,还是请邵先生开个价吧。”
邵掌柜再次闭上眼睛,拿手推推玳瑁眼镜,睁开眼后,开口说,“在商言商,按现在的行市,怎么也得这个数。”说着,伸出三个手指。
“三千?”甄永信吓了一跳,“当初邵掌柜,只花了六百五十两,几年工夫,就要三千,合适吗?”
“是呀,”邵掌柜靠在椅子上,懒洋洋地说,“现在房子升值了,再说,我买下后,又做了修缮,也花了不少钱。”
“可总不至于三千吧?”
邵掌柜开始不乐意了,沉着脸说,“邵家的济世堂,也不是才开了一年两年,你也是城里的老住户,也该知道,济世堂多暂和别人讨价还价地卖过药?”
“卖药怎么能和卖房子一个样呢?”甄永信反问道。
“怎么不一样呢?”邵掌柜也毫不相让,“在商言商,行情就是这样,求之如金玉,弃之如草芥。你看那些草药,原本就是生长在荒山的野草,平时你到山上走走,可能随手就可采下一棵,随手就丢掉,可是一经采药人采来,洗净、晒干、切片、炮制,放进柜中,它就成了有价值的东西,有的便宜,有的贵得不得了;有时这种药贵,有时那种药贵,你说它到底值不值?谁都说不清楚。”
甄永信忍着气,听邵掌声柜高谈阔论,一等他说完,就商量道,“邵掌柜也把价要得太狠了些,给个合适价吧。”
“狠?”邵掌柜生气了,“那就请甄先生自便吧,反正城里有的是房子,何必老盯着我这处?一口价,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甄永信嘴唇哆嗦地离开了济世堂,胸口像遭了谁的一闷棍,又痛又闷,憋得透不过气儿,虎着脸回家,见谁也不搭理。妻子收拾午饭时,问他和谁怄气,他只是摇头,不敢发作,胡乱吃了几口闷饭,就推说困了,躺到炕头睡下。
昨晚睡得透彻,今天就不怎么困了,躺下后也睡不着,等妻子把碗筷收拾停当,在锅台上刷碗时,他就躺不住了,爬起来出了门,顺着大街往西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