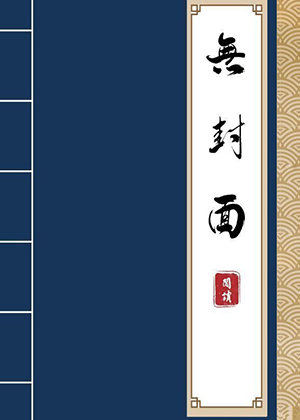“这小姑娘……”陆茗看了我一眼,也许是看不到他想看到的东西,便只说了半句话,自斟了酒,自己饮下。
我虽然不会娶隐歌,但是身为定远侯的儿子,自然有一些官面上的手段,要替她解除这段婚约,并不是没有法子。我这样同隐歌说,隐歌却只笑一笑,说不必。
那笑容里的苦涩,让我意识到,这个小姑娘——这个没有心事,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像是在一夜之间,忽然长大了呢。
一个人长大,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瞬间,我遇见绾衣的那个瞬间,或者隐歌遇见我的那个瞬间,鹰忽然折了翅,刚出窝的小黄鹂忽然停止了歌唱,于是人长大了,有了忧伤和烦恼。
她暂时借住在我的木屋里,但是有时候会下山,不几日又回来。
她再没有问过我,如果她离开,我会不会难过,会不会想她。
日子又回到从前,练剑,日复一日,晚上回来看到木屋里的灯,像是燃在心上,有一点点的暖,但是隐歌面上常挂的笑容,已经不见了,话也少了很多,逮兔子的本事渐长,已经不需要我帮忙。
山里的星星格外明亮,有时候我问她会不会想家,她说会,但是她不想走。我于是叹一口气,说:“我的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隐歌,我要下山去了,以后……你不要一个人留在这里。”
山中这样寂寞,这个爱说话爱笑的姑娘,想必是耐不住的。
她转头来看住我,良久,摇头道:“不要紧的。”忽然又跳起来,说:“你就要走了,我烤只兔子给你吃吧。”
这样诚恳,我点头应了一个“好”字。
“然后你就下山来了?”
“没有,”我看了一眼桌上东倒西歪的酒坛,一时间竟然数不清楚,不知道喝了多少下去,“当然没有,她怎么会……这样轻易放我下山?”
“你是说……她……下了药?”陆茗再一次张大嘴,想来这个消息比我爹是定远侯更让他吃惊,谁说不是呢,谁还记得,初见时候,那个鲁莽和快活的隐歌?我怅怅地想,觉得手臂上被她伤过的那个位置,又隐隐痛起来。
陆茗猜得没有错,醒来时候我发现我被下了药,然后又被制住了奇经八脉,气不能行,莫说下山,就是在左右转转都有困难。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会让你走,重华,便是你不肯娶我为妻,我也绝不会让你走!”
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让我恍然想起她被唐门弟子围攻的那个晚上,那样倔强和坚定,我忽然发现,原来我还是小看了江湖人——便是这样不知世事、没心没肺的一个小姑娘,身上也是有这样重的匪气啊。
我从心里生出厌恶来,扭头去不看她。
她也不觉得气馁,每日里做自己的事,就像平常一样上山砍柴、逮兔子,或者有时候会逮到大一点的动物,于是我知道她下毒或者使暗器的功夫又有了长进。
这样的日子过去很多天,到底有多少天,我也已经不记得了,隐歌是那样固执的一个女孩子,任凭我怎样发怒、怎样生气、怎样怒吼如雷,都只笑着看住我,说:“我不会让你去的。”
“可是你这样,当真能留住我吗?”我冷冷地看住她,“便是留得住我的人,也留不住我的心啊。”
“那又如何?”她微笑,“留不住心,留下人也是好的。”
她总是笑着的,可是有时候我深夜里醒来,会看见她一个人呆坐着看月亮,有清亮的眼泪,缓缓流下来。
这时候我又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知道,她原本就不是什么坚强的女孩子,以前上山,被老虎和狐狸欺负的时候,都会气得掉眼泪,但是那时候还有我,而今……
可是我答应过要带绾衣走,她是我年少时候所有的梦想……隐歌,而隐歌,你我终究不过是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的两个人,怎么会生出根?我这样想的时候,忘记了我与绾衣,也不过是萍水相逢。
而时光是这样可怕的一种力量,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会这样不死不休地纠缠下去,从天荒地老,到地老天荒,这样想,又让我觉得惊悚。
因为我还要下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