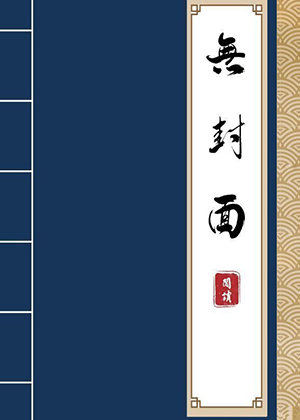我要下山,如同被缚的鹰要挣脱牢笼。
于是有一日,忽然有大批的人马上山来,设下陷阱,隐歌一进屋,就落进了天罗地网,她惊慌地四下里张望,看见蜷在角落里的我,大声道:“你快走!快走!”
但是忽然她又落下泪来,也许是意识到我手足被制,根本就逃不出去。
她哭得这样伤心,伤心得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将弃她而去,我再装不下去,便只慢慢站起来,然后看到她惊讶的目光,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说:“隐歌,我终究是要走的,你知道的。”
——是我放出的消息,让驻守蜀川的将军派兵来救我——父亲的孩子虽然多,我也不是爵位的继承人,但是事关侯府颜面,自然会有人来救我。
也是我设的局。
到这一步,她反而镇定下来,点头说她知道,泪痕还在眼角,宛然,目光里却又生出坚定的颜色,她说:“重华,你不要走,即便你走出这里,千山万水,只要我不死,我就会把你抓回来。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苦笑,“那么,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我?”
“我是江湖人,”隐歌道,“江湖人在碰上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最后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比武,一对一,生死由天。
我于是应了她。
我让所有的人都退了出去,木屋之中就只剩下我和隐歌,我遥遥想起初见时候,被一脚踢开的门,那个全身挂满雨珠,像个竹绿色大粽子的小姑娘,她那样天真,那样鲁莽,为什么有一日,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兵戈相见,不死不休?
但是她的刀已经到眼前,我退一步避开,长剑出鞘,斗室之中,忽然有刀光隐隐、剑气森森,我从来不知道,隐歌的武功,竟然在数月之间,精进如斯——也许是为了保护我?这样的念头,连我自己也觉得荒唐。
最荒唐的大概是,这是一个事实。
这只是一个事实。
我侧身又躲开一刀,但是她忽然一步踏进,刀光一缩,袖中打出满天花雨,金针晃花我的眼睛,我的剑也到了她的喉间——这原本是我与她都练惯了的招式,看似惊险无比,实则有惊无险。
只一错步,又过一招。
我忽然又想起她在山顶给我喂招时候的事,我们低头找散落的金针,那时候的阳光,那时候的朝霞,那时候和阳光一样明亮的眼睛,和朝霞一样鲜艳的笑容。
心下戚戚。
而她又逼近一步,我照例要退,脚跟已经抵到墙面,竟是无路可退了,眼看刀风已经扑到面上——她竟是要杀我吗?
她竟是真的要杀我吗?
我恍惚地想,恍惚再不能自持,剑气如虹,剑光如雪,在退无可退的地方猛涨三尺,刹那之间,有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我一身白衣。
隐歌摇摇就要倒下去,我一把抱住她,我问她为什么,你当真要杀我吗?如果不是,为什么逼我到这一步?
她艰难地笑一笑,说:“你说得对,我留得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可是重华,你不知道,只要我不死,我就会留着你的……我情愿你恨我,我情愿你死,我也要留下你。”
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她的手就垂了下去,再不能睁开眼睛,然后身子慢慢就冷了。这一次,她没有问我会不会难过,没有问我到底有没有爱过她。
有没有?
我茫然地问自己,茫然地不知道怎样回答。
“她……死了?”陆茗呆住,连酒坛里的酒洒了一地都没有在意。
“死了。”我低声回答他,也低声回答自己,她已经死了,我亲手葬的她,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具冰冷的身躯,曾经陪伴我那么多个日夜……那么多,我并不想杀她,我甚至都不想伤害她。
可是明明也是我这双手,将她斩杀于剑下。
我狂奔下了山,不敢回头看一眼,也不敢去问自己,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谁,让我们走到这一步,再不能回头?
我抱起酒坛,猛地喝几口,酒并不烈,至少它不能让我醉去。
忽然又听陆茗问道:“这样说,你这一次进京,是想……”
“是想进宫。”我淡然说出我的答案,因为我再没有别的事可以做,除了进宫,找绾衣。
陆茗看看我,又看看空空的酒坛,忽道:“你要进宫,找的人姓余?”
“是。”
“余尚书的女儿——我猜得对也不对?”
我惊奇地看住他,不知道一个草莽丛中的江湖人,如何知道皇宫大内里嫔妃的名字,他见我这般模样,想是不必再问,便又多喝了一口酒,忽道:“我只是忽然知道了,为什么隐歌宁肯死,也决不肯放你下山。”
“为什么?”
“她怕你伤心。”
我呆呆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只道:“你回京,问问皇帝,自然就会知道为什么。”
“余嫔啊……”
平郡王柳洛——如今他已经是皇帝了,他带我至一座宫殿前,我推开宫门,锦绣堆里端坐着一个人,嶙嶙白骨,眼睛的地方深深陷下去,让人觉得,如果她在生,那双眼睛一定很黑,很亮。
“已经死了很多年了,难为你还记着。”他说。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我忽然想起隐歌来,想起初见时那只湿淋淋的大粽子,想起她一个人在木屋里等我归来,想起她说要上山打兔子给我吃,想起她在同门围攻之下那样倔强和刚强的神色,想起她说不放我走,想起她一个人在没有星光的晚上落泪,也想起她最后说“我情愿你恨我”。
想起陆茗问我:“你恨她吗?”
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看到了陆茗写的那本《武林外史》,那本书里提到我,他说我在青藤镇上与他对饮,喝得大醉,醉梦里一直在喊一个人的名字,起先他以为会是绾衣,后来才发现不是,我叫的是隐歌。
隐歌。
这时候我已经垂垂老去,一个人,在青藤镇上,一壶酒,酒醉的时候会恍惚看到那个穿竹绿衣裳的女孩子,大刀金马地坐在我的对面,我张口要叫她的名字,她抬头来,对我笑一笑。
那一笑之间,所有所有,都灰飞烟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