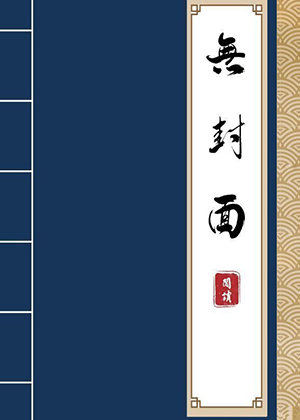她并没有去想柳洛会不会不打算救她了,她对他有种天然的信任感,他可能恨她,但是绝不会不救她。
她在斗室中来回走几步,用脚去丈量,这间房横走十步,竖走也是十步,梳妆台靠墙放置,左走三步,右走也是三步,她觉得有趣,便在梳妆台前的矮凳上坐下来,镜子里映出她的面容,往左看是墙,往右看……她目光一呆,右边墙上竟然密密麻麻都是字。她惶惶然站起,又慢慢坐下,想道:前晚上柳洛和秦祢所见都是这墙上的东西吧。
那墙上的字似的流动的,她稍一走神,字迹已与方才不一样,便敛了心神,字字看去。
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大片乌云积起来,滚滚,不断有雷鸣,闪电,眼看就要下雨了。容郁看得很是吃力,唯有闪电时候字迹才清楚一点,但那清楚又有仓皇的底色,时隐时现,她不免想道:那墙后到底是什么呢?
墙上横竖有百字上下,似是一封留书,留书人叫唐敏,却没有写出收信人的名字。留书上说:我唐敏将与平懿王决战于西林塔,无论平懿王是生是死,我都不会活下去;西林塔便是我与柳毅葬身之地,相信你能明白。这封留书,别人看不到,你一定能看到,所以我还有一句话留给你:我死之后,所有过去的事都让它过去,唐门与柳家的恩怨到此为止,你要做什么,都听从你自己的心,不必再听从任何人。
容郁反复看了几遍才能够把文字理通顺,她想道:唐敏不知道是什么人,违命侯府并不是人人都能来的地方,她姓唐,莫非书信是留给琳琅?她说让她忘掉以前的事,自己选择,这口气……倒像是她的长辈了,琳琅的父亲早就死了,唐门也被族灭,唯一留存的只剩下她的母亲,那么唐敏……最可能的身份就是她的母亲。
假设唐敏是琳琅的母亲,因知道多年前唐门被灭以及丈夫被杀一事与平懿王有关,约平懿王来此地决战,抱了必死无回之心给女儿留这样一封书信,倒也是说得通……如果是唐敏杀了平懿王,那么琳琅和平留王之间的恩怨可真够瞧的,难怪柳洛面色这样难看,不肯说实话。而秦祢只看到西林塔十三层和子时三刻这几个字,他求财心切,误以为是藏宝之地……子时三刻,西林塔上不知道又设了什么机关呢……不过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二十年……可是二十年后所有人都还困在这个局里,没有谁能够忘掉。
这就是琳琅遗书上所说“母亲愧对唐门,矢志复仇,其间种种,不忍追述”这一段了吧,唐敏何止是矢志复仇,她以命换命,根本就是死志已坚,才换得“大仇得报,元凶伏诛”,难怪琳琅说“不忍追述”。
可是如果平懿王当真在此一役中死掉,后来又是谁让琳琅用上“七伤”之赌呢?连她自己也说“元凶伏诛”之后诸事已了,无须追究,那么还有怎样的深仇大恨让她不惜自残本身来达到求胜的目的?
她是在求死,也是在求胜。但是如果人死了,那胜利又为着谁呢?忻禹,还是平留王?
唐敏让她听从自己的心,她最后选择嫁给平留王,可是最后赢得天下的是忻禹,是不是说——她爱的是平留王,所以将江山拱手赠与忻禹?否则以当初柳氏的权势,输掉这一仗委实可疑。
但,如果让忻禹自己来选,恐怕他选的也是江山而不是美人吧。
然而在这一个时刻,她竟然觉得忻禹可怜,十分可怜,他痴恋了数十年的女子,宁肯用江山来换自己的自由,也不愿伴他一生一世……那样伶仃的一个男子……
她胡思乱想了一阵,因心中有事,时间倒好过一点。
到中午大雨已经下下来了,雨声轰隆如瀑布。
余年送饭菜过来,神色间欲言又止,她知道在几人中他虽然神色最狠,实际却是性情中人,所以有时候对他笑一笑,忽然道:“我在翠湖居的时候身边有个侍女叫知棋的和我最好,听说小名也叫云儿。”她以为他会动容,然而并没有,他照常等她吃完东西,收食盒下去,反是临走时候说了一句:“娘娘这话若是让别人听去了,你我都走不出百步。”
容郁听这话,心里不由稀奇,想道:秦祢手下能有多少人,加上江湖上的帮手,难道还能多过西林寺的和尚去?
雨下了一天,到晚上反而出了月亮,容郁熬到子时,月光偏西,她将矮凳依次翻过来,原来背面贴有一层极薄的膜,字就写在膜上,最难得这层膜的质地与木质相近,用手摸去,浑然一体,根本觉察不出来。因是贴在矮凳背面,光线不容易照到,即便照到也多半角度不对,即便角度对了,也没那么巧刚好有人看到,容郁心中暗道一声“厉害!”,静了心去看那些字文,竟然是一本毒经。
她觑准了接口,将膜一片片撕下来,靠近窗边去看。
月光尚好。
容郁迅速翻到其中有“胭脂醉”的一页,内有详细解说,原来胭脂醉同一种植物的花和叶,这种花叫泪美人,洁白,倒钟状,平日里也有人养来观赏,一串一串垂下来如零碎的星,在月光下分外好看,性辛温,花没有毒,叶有微毒,多食会致使失明。花与叶同根而生,所以相生相克,胭脂醉就是以花入茶,以叶熏香,熏香满室,离之则醉。容郁往下看,书中详列了解毒的办法——竟然这样简单啊,容郁也不由叹了一口气。
门外传过来轻微的一声咔嚓,因为太静了,所以竟然让她听得十分分明,她迅速将毒经卷起来藏于袖中,门缓缓推开,是余年。
他说:“如果你今晚走,能够去哪里?”
容郁想也不想,脱口答道:“西林寺。”她并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此地距京城有万里之遥,即便到了京城,离她的翠湖居也还有万万里之远,诗书上说:刘郎已恨蓬山远,更远蓬山一万重——要到她这个地步方知道什么叫无路可走,无处可去。
余年说:“那好,我送你去西林寺,我们只有一刻钟的时间。”
容郁知道秦祢等人必是去了西林塔寻宝,侯府中人手空虚,所以他才敢说这等话。她盯住他问道:“你为什么救我?”
余年掏出钥匙来开锁,一边说道:“我帮不到云儿任何事……你心地好……”这两句话没头没脑,容郁却是听明白了,所以她轻轻地说:“你放心。”
他抬头来笑一笑,说道:“虽然先人为守护和夺取宝藏流了很多的血,可是并不是说宝藏就是我的,或者说宝藏有我的一份,我不想像先人一样,继续为它流血,因为我并不是非要它不可,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说得并不流畅,但是意思很明白。
钥匙对准插口,轻微的一声响,余年又从口袋里取出药丸来,容郁接过来一仰首咽了。
夜风里仍带了雨后的清新,路上没什么人,容郁几乎想大喊几声:我终于出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