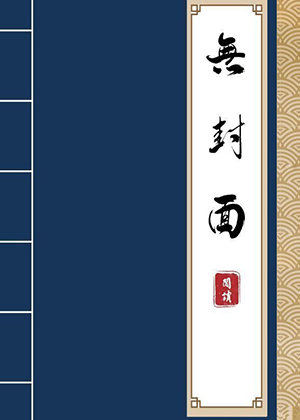苏心月行了一礼道:“公子过谦了。”
青衣少年凝神看了看苏心月,面上放出光彩来,道:“早听说苏姐姐的名字,不想姐姐不仅歌艺名动京师,竟还有如此天香国色。”苏心月连说“不敢当”,少年轻轻一笑,指如轮转,面容隐在琵琶之后,仿佛蒙了层纱,教人看不分明。
这曲《水调》竟又与前次不同,前次《琵琶仙》听来只觉浓丽妩媚,如女子的胭脂,未免有缠绵悱恻之色,这曲《水调》竟是一洗靡靡,清丽皎皎如月,不沾些许烟尘,听得一干人默然,想起五湖烟景,泛若不系之舟。
一曲罢。
众人尚未回过神来,少年已经收了琵琶,到柳言身边,轻唤一声:“爷——”柳言别过脸笑一笑,有纵容的意味,随即起身告辞。少相道:“不意小王爷有如此雅兴,改日必前来拜访,还希望小王爷不吝赐教才好。”柳言应他:“好说、好说。”拱手而去,竟是不肯亲口相邀。
青衣少年与柳言走出去老远,柳言问他:“真是爹找我吗?”那少年低眉道:“知道瞒不过爷去。”柳言敲她一记,“找我也就罢了,干什么这么鬼祟在楼下弹琵琶,引得一干人注目?”少年道:“那霜思林岂是好去之处,琳琅可不想找爷一次搭上俩月月钱,那还教不教人过日子啊,爷体谅些。”柳言道:“这张嘴啊,真不知道怎吗生的……不和你绕弯子,直说,什么事?”
琳琅道:“昨晚青芷园走水,波及宁语阁,结果……”
“宁语阁……你昨晚不在?”琳琅的头垂得更低些。柳言似是想起什么,一顿脚道:“糟了,昨晚我也不在!”
琳琅看他一眼道:“你也想到了。”柳言道:“那你还诓我回去,不行,我得找个地先避避风头。”
琳琅抬眼看了看,“来不及了。”远远见一骑绝尘,不是懿王府侍卫统领路非却是哪个。琳琅往后缩一缩道:“爷你对付着,琳琅先行一步。”柳言一把拉住她,咬牙道:“你昨晚到底去了哪里?”琳琅婉转一笑,生生把个小王爷笑得酥了身子,“昨晚……不是爷带了琳琅去秦府弹曲吗?”柳言惨叫:“你不会和爹也这么说吧。”
琳琅道:“不然如何——”忽然失声叫道:“哎呀——”柳言心神一分,一转头,哪还有琳琅的影子。却是不恼,嘴角反生出一丝笑痕,“你下的套,把自己绊了可别怨我。”
那是他们第一次相见,他站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以为只是旁人的一场戏,很多年以后他才知道,那是他的劫。
“琳琅是我师妹,我们不过一些棋子,进退生死都在下棋人手中,我们的命,是天底下最不值钱的。琳琅特殊,只因她进了平懿王府,不幸小王爷爱上她。”
容郁暗想着“不幸”两个字,以身份论,明面上琳琅只是琴师,实质也不过是某位达官贵人手下死士,能够一步登天到王妃的位置,又何来不幸之说?思及于此,不由脱口问道:“那么,谁是你们的主子?”
怪人似是凝思了很久,方才缓缓答她:“当时他是柠王,如今,是天子。”
容郁身子一震,原来平留王妃与忻禹有情在先?他竟舍得将自己心爱的女子送入另一个男子的怀抱!她恍惚地想起来,传说中有个叫夷光的浣纱女,她在若耶溪畔遇见她爱的人,可是这个男子亲手将她送给敌国的君主,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原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耻辱要那样弱质的女子来承担——原来他的野心与欲望要他最爱的女子用身体来成全。容郁把身子蜷起来,她觉得冷,可是并没有昏过去,坚韧的神经支持着她,“那么,到底是谁杀了她?”她隐隐猜到答案,但仍是抱了最后一线希望,无论多少人告诉她是忻禹杀了琳琅,可是只要有一个人说不是,她都相信。
那怪人的身子竟是震了一下,“谁杀了她?”语气里诸多的怀疑和不肯定,然后呆住,站在月光里,如风沙侵蚀的石雕。
“难道不是皇帝下的手吗?”容郁等了很久,终是没能忍住,出声问道。
“皇帝?你说柠王?他?……他怎吗会杀她?不会的,不会是他。”怪人的语气先是充满了疑问,但后来说到“不会是他”竟是无比肯定。
“为什么不是他?”
“如果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追查的凶手……难道竟会是他自己吗?不是,当然不是!”怪人急促地重复着“不是”两个字,像是要说服她,但更像是要说服自己。
“你是说,这么多年,皇上一直在追查平留王妃的死因?”容郁不疾不徐地问。
怪人疾退三尺,惊问道:“你……你怎吗知道的?不,不是他,绝对不是他!”他口中念着“不是他”疾速转身冲了出去,片刻就不见了踪影,容郁一个人躺在床上,空空荡荡,仿佛整个宫殿都在回响那个怪人的话:“不是,绝对不是他!”
或者真的不是他吧。容郁长长出一口气,看看更漏,还不到二更。
容郁有身孕的事不过几天就传遍后宫,闻者无不惊疑,翠湖居住过那么多嫔妃,能怀上孩子的,容郁却还是头一个。人人口中不言,心里却都转出一个念头:难道皇帝竟舍得连孩子一同送去关雎宫不成?此念一生,姿态自然不同了些,翠湖居里人来人往,甚是殷勤。
知画战战兢兢,唯恐有个不对被容郁发配了出去,知棋见了只是冷笑。
这一日天和气朗,没有人来访,难得清净,容郁换了宽大的衫子,叫知棋扶她到无心亭去。寒烟湖里的莲打了大大小小的苞,衬在深碧的莲叶里,煞是可爱。容郁隔栏看着,忽然回头问:“知棋,这亭子为什么叫无心亭?”
默然侍立一旁的知棋脸色变了一变,答道:“是皇上起的名,至于为什么,知棋却是不知道。”
容郁懒洋洋地看她一眼,道:“浑丫头,在我面前也要说谎,你若是当真不知,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
知棋下意识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脸,眼帘一垂,默了半晌,道:“娘娘当真想知道?”
容郁揉碎手心的花,丢下湖去,一群大尾巴红鱼摇摇摆摆游过来,吐出一串一串的水泡,容郁沉沉地露出一个笑容,“你说呢?”容郁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与声调与平常并无二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知棋看着主子的背影忽然觉得阴森,她倒吸了口气,慢慢地说:“九年前,住在翠湖居的是余嫔。”
“余嫔小字绾衣,礼部尚书余郓之女,自幼就有才名,琴棋书画无不出色,十五进宫即封嫔,不出两月入主翠湖居,万千宠爱集于一身,莫说妃嫔,便是皇后见了也让她三分。她少年得意,难免娇纵,得罪人而不自知。那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迁怒于翠湖居的木槿林,嫌那木槿白得晃眼,叫侍从将那林子毁了,底下人在宫里做老了的,都知那林子是皇后心爱之物,如何敢轻举妄动,余嫔愈恼,竟亲自动手,将那林子砍得七七八八,底下人一见不好,忙偷偷通知皇上,皇上听闻此事,面上也没有变色,只是自那天起绝足翠湖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