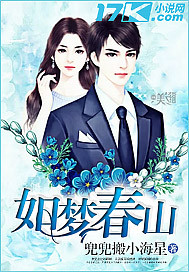石攀山公墓还不那么成规模的时候,庆州最兴旺的墓地是在城南。
卢韵姮一身黑色的衣裙,长发盘成了髻,发髻一旁别着一朵纯白的栀子花。
虽然是白色素净的颜色,但却有着最透彻又浓烈的香味。这花似乎不合时宜,但却是他最爱的花。
卢韵姮看着屋子中央挂着的照片,浅淡的眸色里,蕴着最浓烈的悲哀。
十八岁的何莞尔,在空气里寻找着若隐若现的那一丝芬芳,和十六岁的卢含章、九岁的何一笑并排站着,有些恍神。
五点半开始的告别仪式,她看着一队队穿着警服的人,对着灵堂正中的冰棺敬礼、鞠躬,然后右转、走到他俩面前。
然后,他们一家人鞠躬答谢,听着那一声声的节哀后,又继续换下一波。
何莞尔也抬头,看向了灵堂中央。
那里是一簇簇白菊拥簇着的冰棺,里面身披国旗躺着的,是何莞尔与何一笑的父亲。
他已经过世一个月,经历了解剖、冰冻,现在终于可以入土为安。
可是一个月的时间,何莞尔还没能从失去父亲的痛苦里缓过来。
天亮以后,父亲将被火化,化作一抔灰白色的粉末,被装进一个小小的罐子里。然后,在一块深黑的石碑后长眠。
这就是人最后的归宿吗?活着的时候再顶天立地,也终究得躺在咫尺之间的地方,饿了、冷了、累了、孤单了,也没办法和亲人述说。
何莞尔悲从中来,眼泪又一次地忍不住。
何一笑轻轻拉了拉她的手,悄悄说:“姐,妈妈说过,不要哭,不吉利的。”
何莞尔忙抹了把眼泪,怕惹卢韵姮不高兴——已经没了爸爸,如果妈妈不收留她,那她是不是就成了孤儿了?
冯局长冯坚带着一家老小,在六点左右来的。
正值由上而下严厉的大检查,因为让毒贩逃跑还到派出所夺枪,原市局局长引咎辞职,他暂行局长的职务,目前的状态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冯坚身后是跟着个白衬衫、黑短裤的男孩,还有他的妻子。
冯昔也很忙,因为还有半个月就是高考了,何莞尔知道学校里现在必然是在做靠前的最后动员,气氛十分紧张。
冯坚鞠了躬,特意上前扶着冰棺看了眼何邵阳的遗容,然后来到了何莞尔面前。
他眉目间是难掩的悲意,声音里带着一丝鼻音:“笑笑,别怕,你爸爸走了,但还有冯叔叔在。以后有什么难处,你直接来找冯叔叔,不管多大的事,冯叔叔都帮。”
何莞尔点着头,泪水又充盈了眼眶,随着她点头的动作,一滴滴砸向了地面。
“不要哭,忍住。”
耳边响起冷清的声音,何莞尔知道,那是卢韵姮在说话。
按照卢韵姮老家的规矩,亲人横死是不允许哭的,否则亡者在地下,将不得安宁。
卢韵姮确实严格按照这条不知道哪里来的规矩在做,不管人前人后,何莞尔都没看到她掉过一滴泪。
可是何莞尔做不到,好几次伤心落泪,还一边哭一边责怪自己不够坚强,不能让爸爸安心地走。
好在这一次她及时地忍住了,没有听到卢韵姮的叹息声。
从火化到下葬,整整三个小时。
何莞尔看着太阳升起,看着烈日当空,看着父亲化作一个小小的盒子,被关在一个稍大的盒子里,永远见不到太阳了。
她一次次告诫自己一定要忍住不要哭,好容易撑过了长长的仪式。
骨灰落葬,石碑立起,来送行的警察不烧香不焚纸,只在墓碑前一批批郑重地立正、敬礼。
何莞尔看着他们一批批地离开,然后和何一笑并排跪在地上,焚烧着纸钱。
共产党员都是无神论者,但家人不是——卢韵姮坚持着这一套传统的下葬仪式,焚完香蜡钱纸,再点燃一串长长的鞭炮,最后烧掉黑色袖套和孝帕,这场葬礼才算结束。
大概是准备的钱纸放在地上过了两晚上,那面沾染了潮气,一点燃就冒着浓烟,熏得何莞尔眼泪直流。
卢含章跪在她的对面,也被熏得眼泪汪汪。
卢韵姮并没有和三个孩子一起焚烧钱纸,而是倚坐在墓碑的一侧,脸贴在墓碑上,除了眨眼以外,一动不动、面无表情。
然而她眼里浓浓的悲哀,却是何莞尔从未见过的。
她有些愣神,忽然看到墓碑前燃着的一对蜡烛快要倾倒,一旦倒下就会烧到到卢韵姮的衣裙上。
她忙伸手去扶,热烫的蜡油顿时滑到了她的手上。
何莞尔被烫得很疼,下意识地一甩手,手里的蜡烛刚好掉到了何一笑的那边,好巧不巧正巧落在他拖地的孝帕上。
易燃的材质让火星迅速串了上来,顿时引燃了那一串白色的麻布。
何莞尔惊叫着跳了起来,几步上前要扑灭何一笑身上的火,却不料她头上戴的孝帕太长,一下子拖进了火盆。
天干物燥,火星子顺着孝帕也蹿到了何莞尔的身上。
两个孩子身上都腾起了火,四周的人惊呼着上前灭火。
卢韵姮这才从入定的状态中醒过来,扑上来拍打着何一笑身上的火苗,直到他安全无虞,反反复复查看一番,长舒一口气。
何一笑已经吓得大哭起来,卢韵姮一把抱住何一笑:“可吓死妈妈了,妈妈只有你了,你可不能有事……”
一旁的何莞尔身上的火也已经被离她最近的卢含章、冯坚和冯昔拍灭,呆呆地立在原地,身上没受什么伤,只是闻到了一点点,长发被烧焦的味道。
冯坚确认了何莞尔也没受什么伤,长舒了一口气,对卢韵姮说:“按照老传统,孝帕被香蜡点燃是大吉,孩子没事就好,别放在心上。”
卢韵姮木木地点头,依旧搂着何一笑,久久不肯松手,却看都不看何莞尔一眼。
冯坚暗叹了口气,吩咐冯昔:“昔娃子,你弟弟妹妹怕是吓到了,你上午请个假不去上课了,在这里陪一陪他们,照顾好卢阿姨。”
他的妻子面露不满,想要开口反对,却被冯坚一眼瞪了回去,只好作罢。
何莞尔则愣在原地,脑袋里反复播放着刚才卢韵姮的话——妈妈只有你?
妈妈只有弟弟——所以,她又算什么呢?
她刚才也被吓到了,却得不到一个拥抱,甚至,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
她这些天一直强忍着的眼泪,忽然间再也忍不住了。
众目睽睽之下,何莞尔坐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
冯坚面露不忍,又拉过冯昔吩咐:“笑笑这些天着实难过,你好好照顾她,爸爸还有公事必须得走了。”
他顿了顿,看了眼一旁黑衣黑裙的背影,压低声音:“你卢阿姨也是,操持葬礼本来就累,还要照顾三个孩子,你多帮衬一点。”
冯昔懂事地点头:“我知道的。”
冯坚离去的时候,一再地叹息,一步三回头,眼里是难掩的悲哀。
一个多小时以后,何莞尔是哭到没有力气再哭,才渐渐停下来的。
这期间,卢含章一言不发,但一只手一直放在何莞尔的手背上。她掌心传来的微暖的温度,让何莞尔觉得,自己也还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冯昔也陪在她旁边,一步都没有离开过,体贴地给她递着纸巾。
那位早上对冯昔留下来颇有不满的周阿姨,一遍遍看着时间,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她踩着高跟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说:“小昔,该回去吃午饭了,只给你请了半天的假,下午还要上课。”
冯昔站起身道别,周阿姨看着周围没大人,忍不住抱怨:“真是的,你爸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你马上要高考,还有什么比学习还重要?又不是什么要紧的人!”
冯昔轻喝:“妈!”
周阿姨挑着眉:“我说得不对吗?”
她一边说着,视线停留在何莞尔的身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
何莞尔怔了怔,刚想要移开眼,下一秒,却和她对视起来。
她已经足够高,虽然瘦,但身高的优势足以弥补她年龄阅历不足的劣势。
十几秒后,周阿姨竟然被她看得浑身浸了水一般冷浸浸的。
她不自在地移开视线,烦躁揉了揉眉心,转身离去。
何莞尔却听到她背过身的那一刻,小声地嘟囔了一句:“一家子狐狸精!”
冯昔目睹了全过程,趁着母亲走远,迅速地在她耳边说:“我妈就这样,你早知道的,别在意。下午我放学过来给你送复习资料,再给你些带好吃的过来。”
何莞尔攥紧的拳头缩了缩,迅速低下了头,心里一个念头悄悄地生根发芽,从此长成了参天大树。
晨光和夜色交杂,一时难分胜负。
何莞尔坐起身,一时分不清是在梦境,还是现实里,直至凌晨透窗而入的寒意冻得她一个哆嗦。
她忙拉过被子裹紧自己,脑子里纷乱的思绪,好容易才梳理清楚。
她竟然做了那个莫名的梦以外,另外一个梦。
只是这一次的梦,是多年前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了,所有细节一一重现。
她梦到了父亲葬礼的那天。
虽然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却如过眼云烟般,她好久都不曾记起了。
那一天,妈妈一袭黑裙,簪着一朵爸爸最爱的栀子花,捧着爸爸穿着警服的照片,以未亡人的身份,送了父亲最后一程。
而在何莞尔记忆里,那是一向娇弱的母亲难得坚强自立的时刻。
之后,因为那场意外的火,因为卢韵姮的冷淡和疏离,何莞尔曾经选择逃避和遗忘那一天发生的事,后来竟然真的渐渐模糊起来,那一日的委屈和伤痛,也渐渐化作了守护家人的决心。
而随着这个梦苏醒的,还有她曾经强行不想去回忆的细节。
比如火化前,妈妈用颤抖的指尖,一丝不苟地给爸爸整理着身上的警服。
还有她虽然不哭不闹,但眉角眼梢却弥漫的浓重的悲意。
那时候的何莞尔,对爱情还很懵懂,可现在,她觉得自己能够读懂了。
那是——永失吾爱。
既然爱得那么深,为什么当初要离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