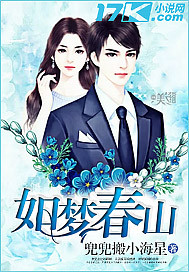那场车祸后,何莞尔已不记得父母当年有多恩爱,但她知道卢韵姮电饭煲都不会用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一直宠着她护着她的老公,是不可能那样的。
成熟是有代价的,只有雨打不着吹不着的小公主,才有资格纯粹得像个孩子。
但是,自从她有记忆开始,关于父母感情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他们关在卧室里整宿的吵架,以及时不时的冷战。
她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但知道一年后,他们离婚了。
然后,一个不娶,一个也没嫁,直至天人永隔。
当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何莞尔很想从回忆里找到蛛丝马迹,然而却没有丝毫收获。
陷在回忆里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何莞尔呆坐了半宿,直到手机的闹钟响起,发现已经六点半。
穿着睡衣坐在床上起码半小时了,她手冻得冰凉,忙洗了个热水澡,吹干了头发,困顿的感觉汹涌起来,人都迟钝了几分。
她眼看着天色亮了起来,却又不想起床,于是干脆自暴自弃起来,再一次钻进了被窝,放松心情,迅速地睡着。
————
大年初一,庆州城内是不许放鞭炮的。
不过总禁不住那些固执于传统的人。
于是从黎明开始就会时不时响起的鞭炮声,虽有几分扰民的嫌疑,不过也平添了几分节日的气氛。
何莞尔没被鞭炮声惊醒,却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
笃笃笃、笃笃笃,声音不轻不重,有节奏又坚定,她想蒙头大睡不管那声音的,没想到起码持续了十分钟也不停。
何莞尔从床上坐起来,吼了一句:“谁啊,真讨厌!”
她睡得半梦半醒,很不想起身去开门——摸出枕头下的手机看了眼时间,也还不到十点。
她怒气冲冲抱着膀子坐在床上,赌气一般不肯去开门,又过了一会儿,敲门声没了。
何莞尔长吁出一口气,缩进温暖的被窝,结果都还没来得及闭眼,笃笃笃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啊!”何莞尔黑着脸从床上坐起来,彻底清醒了。
笃笃笃……
“谁啊谁啊谁啊!真烦!”
她大吼了一声,气势汹汹地下了床,跑卫生间里拿帕子胡乱抹了把脸,接着随手抓起一件外套披在身上。
然后,十秒内横穿过客厅,大力拉开了防盗门,吼了句:“谁!”
莫春山看着眼前的人,微虚了下眼睛,接着抬腕看了看表:“我敲了半小时。”
何莞尔的起床气镇铺天盖地,这时候别说莫春山,天王老子也敢怼的。
于是冲着他吼:“你有病啊,你啄木鸟吗你?大早上的不去捉虫你扰什么民啊?森林里不够你放飞自我那你去玩摇滚玩定音鼓啊,敲个门还带节奏的你咋不去网上接受敌资当水军头子呢……”
她嘴里噼里啪啦一长串稀奇古怪又刁钻的骂人的话,莫春山就那么听着,同时也在打量着她。
看得出来她刚起床——穿着件黑色的羽绒服,没扣扣子,但因为宽大还能掩住里面的一套睡衣。那睡衣大概洗了太多次,已经分不清是粉还是白,材质也不大好。
头发毛毛躁躁,脸还有点肿,眼圈微红。半张脸刚好被楼道窗户透过的一缕阳光照在上面,皮肤白到发亮。
等看清楚她的脚,他皱了皱眉。
她竟然光脚跑来开门?
莫春山绕过她进了屋,直接到玄关,立定、弯腰。
何莞尔顾着骂人,一时不防被他进了门,然后看到他在玄关的鞋柜打开,从里面拎出一双拖鞋,放在她面前:“穿上。”
声音里带着些不容置疑的语气,何莞尔下意识按他说的做了,都穿好鞋子又反应过来——这里是她家,凭什么他来喧宾夺主?
她万分不服气,但也不能把温暖的拖鞋蹬掉,于是被起床气逼出来的气势顿时腰斩。
她垮着脸双臂环在胸前,掩住没穿内衣的尴尬,说:“这位先生,我还没请您进来您就私闯民宅,不知道您有何贵干?”
莫春山看着她,双手插在裤兜里:“我有些事,想麻烦你帮个忙。”
“我还能帮到莫总?”何莞尔轻嗤一声,“莫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她知道自己态度不太好,但就是忍不住。
莫春山只字不提之前给她一顶顶大帽子扣在头上的事,一开口,就让她帮忙?
哼!谁答应谁是王八蛋。
何莞尔嘴里心底都碎碎念,莫春山无视她的冷漠带刺,直接说:“和我结婚,骗一个人。”
————
初春的阳光明亮晃眼,大街上节日气息浓烈,满目高悬的红灯笼将商场装饰得犹如庙会现场,然而人却不多。
也是情有可原,大年初一,不到十一点,很多除夕夜守岁的人还没有起床,能有客人已经算很不错了。
何莞尔坐在商场一楼临街的kfc里,享受着从玻璃照进来的阳光,啃着汉堡喝着可乐。
她是真饿了,但一般情况下她是不会吃这些垃圾的洋快餐的,如果吃了,要么是落难,要么是心情不好。
显然,今天属于后一种情况。
莫春山坐在她对面,一面看着她吃,一面说着他今天来找何莞尔的目的。
一大早被莫春山找上门,何莞尔是死活也不肯让进屋里坐的,更何况他提出那么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
于是便和他来了这里,公共场合嘛,人来人往还有摄像头,就不怕莫春山诬陷她勾引他了,呵!
莫春山要求何莞尔和他结婚的背后有个很狗血很老套的理由——简而言之,莫春山的姨妈骨癌转移,还有最后不到三个月时间的生命。
莫春山说,他的姨妈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牵挂的亲人了。当年他“被死亡”一事,也是因为姨夫的过错,姨妈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他们母子消失几年以后,才偶尔得知自己丈夫参与其中。
长年的抑郁使她患上癌症,几年前曾经治疗过一次,当时效果还不错,却又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心、自责,所以往很不好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了绝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