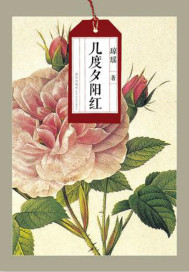黄桷树茶馆在艺专附近,是学生们课余聚集之所。在艺专旁边,专做学生生意的茶馆共有三个,一个被称为校门口茶馆,位于艺专大门之外。一个在男生宿舍旁边,称为邱胡子茶馆。顾名思义,这茶馆老板一定是个大胡子,但是,却并非如此,那老板一点胡子也没有,为什么竟被喊作邱胡子茶馆,其来源已不可考。再一个,就是位于黄桷树的黄桷树茶馆了。当时,泡茶馆成为一种风气,学生们一下了课,无论黄昏、晚上、中午、早晨,都往茶馆中跑,二三知己一聚,泡杯茶,来一盘花生米什么的,海阔天空地聊聊,成了一大享受。茶馆中都不止卖茶,还兼卖酒、小菜和小吃,所以,假若有时间,很可以从早在茶馆中待到晚。而茶馆老板,也很能和学生们结交,赊账是习以为常的。尽管身上没钱,也可以在茶馆中一待数小时。因而,茶馆与学生几乎是不可分的。
南北社成立了将近三个月了,每星期一次的聚集使大家都混熟了。沙坪坝两岸的茶馆,更是个个吃过,老板们一看见他们进门,都会眉开眼笑,因为:第一,他们可以吃空一座城,毫不保留。第二,他们都付现款,概不赊欠。第三,他们的笑闹高歌可以使满座注目,而弄得整个茶馆里都喜气洋溢。
这天的黄桷树茶馆又成了嘉宾云集之处,南北社的社员们大吃大喝,闹得天翻地覆。四宝之一的大宝表演了一幕用鼻尖顶筷子,他把一支筷子顶在鼻子上,又把一个茶碗盖放在筷子的顶端,颤巍巍地在满室行走,看得人人心惊胆战,为他捏一把冷汗。但他却满不在乎,一面走还一面做怪样,走着走着,他从眼角看到那个茶馆的小伙计也张大了嘴望着他,他停下来说:“小伙计,别愁,茶碗盖打碎了赔你一个!”
话还没说完,那筷子一歪,茶杯盖滴溜溜地落了下来。正好特宝坐在椅子上,仰着脸望着那茶碗盖,这盖子不偏不倚,就正正的落在特宝的脸上。特宝“啊”了一声,伸手去接,没接住,然后是东西落在地下打碎的声音。小伙计翻翻白眼,摊了摊手,说:
“好了,赔一个吧,还是打碎了。”
“唔,”特宝*了一声,捧上了一个茶碗盖,哭丧着脸说,“盖子没碎,碎掉的是我的眼镜!”
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得前俯后仰。特宝拾起了眼镜,看看只碎掉了一片,就依然戴到脸上去。大宝还想继续顶筷子,特宝两手一推,嚷着说:
“罢了,罢了,留一片眼镜给我吧!”
大家又笑了。何慕天一声不响地已经喝了差不多一壶酒,从酒杯的边缘望过去,他看到梦竹带着个若有所思的微笑,似关心又似不关心地望着那笑闹的一群。杨明远在和小罗谈论中国人的陋习,只听到小罗大笑着,用他特有的大嗓门说:
“……中国人的习惯,请客嘛,请十个客人可以发二十张帖子,预计有十个人不到;八点钟吃饭嘛,帖子上印个六点正,等客人到达差不多,大概总是八点……”
“假若请一桌客人,发了二十张帖子,预计八点吃饭,而六点,客人全来了,怎么办?”许鹤龄推推眼镜片问。
“那么,一句话,”王孝城说,“出洋相!”
何慕天酒酣耳热,听他们谈得热络,突然兴致大发。他用筷子敲敲酒壶,嚷着说:
“念一首诗给你们听听!”于是,他敲着酒壶,挑起眉毛朗声地念:
“华堂今日盛宴开,不料群公个个来!”
这两句一念出,大家就都笑开了。何慕天板着脸不笑,从容不迫地念着下面的:
“上菜碗从头上落,提壶酒向耳边筛!”
一幅拥挤不堪的图画已勾出来了,大家更笑不可抑。何慕天的眼睛对全座转了转,仍然庄重而严肃地坐着,用筷子指了指外号叫“矮鬼”的一个矮同学,和胖子吴,说:
“可怜矮子无长箸,最恨肥人占半台!”
全桌哄堂大笑,笑得桌子都颤动了,大宝拍着矮鬼的背,边笑边说:“可怜可怜,应该特制一副长筷子,以后参加宴会就带在身边,免得碰到这种客人到齐的‘意外’局面,而挤得够不着夹菜!”胖子吴更被小罗等推得团团转,小罗喘着气嚷:“以后请客决不请你,免得占去半个台子!”胖子吴端着茶杯,哭笑不得。萧燕的一口茶,全喷了出来,一部分呛进了喉咙里,大咳不止。何慕天等他们笑得差不多了,才又念:
“门外忽闻车又至——”
“我的天哪!”萧燕笑着喊,一面用手帕擦着眼睛。
“主人移坐一旁陪!”
何慕天的诗念完了,大家想想,又止不住要笑。何慕天啜了一口酒,抬起头来,感到一对眸子正在自己的脸上逡巡,他跟踪地望了过去,那对澄清似水的眼光已经悄悄地调开了。他怔住,望着那红滟滟的双颊和嘴唇,望着那醉意流转的眼睛和小小的翘鼻子,心头在强烈地烧灼着,举起酒杯,他一仰而尽,握着酒杯的手竟微微颤抖。
“我提议,”萧燕清脆的声音在响着,“我们来做一个游戏:画心!”
“画什么?”小罗问。
“心!我们每人发一张纸,画一个自己的心,心中想些什么,有什么欲望和念头,都要忠头地画出来。假右有谁画得不忠实,我们公开讨论,抓住了就罚他唱一个歌!”
“好,同意!”小罗叫。
画心,这是当时大家常玩的一种游戏,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心形,然后把自己心中所想的都写在这颗心里面,可以把一颗心分成好几格,每个格子大小不等,以说明哪一种思想所占的分量最重。这提议获得一致地通过,于是,每人拿了一张纸,开始画了起来。画了一阵之后,萧燕问明每人都画好了,就把纸条收集在一起,一张张地打开来研究,首先打开的是小罗那张。大家都围过去看,看到的是下面的图形:
“喂喂,”萧燕说,“谁看得懂?”
“我看得懂,”小罗说,“当中的小位置属于我自己,剩下的位置都属于‘她’!”
“她?她是谁?”大家都叫了起来。
“她吗?”小罗慢条斯理地说,“只在此屋中,人深不知处!”
大家面面相觑了一会儿,男同学们的眼光就笑谑地在几个女孩子脸上转来转去,弄得桌上的女性都红了脸,萧燕瞪了小罗一眼,骂着说:
“缺德带冒烟!这怎么能通过?太调皮了,非罚不可!”
“真的该罚!”王孝城说。
“对,要罚!”一致通过。
小罗被大家推了起来,叫他表演。他站在人群之中,用手抓抓头,四面望望,没有一张脸有妥协的表情。看看实在逃不过,他就皱着眉直抓头,把一头浓发揉得乱七八糟,嘴里哼哼着说:
“我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
“我的天哪,”萧燕喊,“你到底唱一个什么呀?”
“唱一个……”小罗眼睛一翻,忽然一拍手说,“对!唱一个也不知道是河南梆子呢,还是河南坠子呢,还是河东河西河北的什么玩意儿。”
“你唱就唱吧,别解释了!”胖子吴说。
于是,小罗连比带唱地唱了起来:
牵马来到潼关,不知此关何名?
急忙下马来看,只见上面三个大字:
啊哈哈呀,原来是潼关!
他还没唱完,全座都已笑成了一团,倒不是因为唱辞的可笑,而是小罗的比划和表情,一句“啊哈哈呀”,眉毛向上挑,眼睛瞪得圆圆的,那股大发现似的怪样惹得大家笑痛了肚子。萧燕弯着腰,喘着气,拼命喊:
“我的天哪!”
好不容易,大家才笑停了。这才继续看下去,下面一张是胖子吴的:
萧燕一下子红了脸,嘟着嘴说:
“这算什么?”
大家又都笑了起来,胖子吴咧了咧嘴,振振有辞地说:
“不是要写实在的吗?我心里只有这个!”
“有你的!胖子!”小罗赞扬地拍拍胖子吴的肩膀,“比我小罗强!”
萧燕狠狠地盯了小罗一眼,脸更红了。
再下面,是特宝的:
“喂,”萧燕不解地问,“蝴蝶梦算是什么呀?”
何慕天很快地扫了梦竹一眼,蹙着眉微微一笑说:
“蝴蝶梦,当然就是蝴蝶梦,我主张通过!”
大家不禁都望了望梦竹,会意地一笑。
梦竹一语不发,长睫毛盖住了眼睛,面颊上漾起一片微红,和天际的晚霞相辉映。
再下面,是杨明远的,打开一看,大家就呆住了!
“解释!”小罗敲着桌子说,“简直是莫名其土地庙!比我还滑头嘛!这无论如何不能通过!如果我还该罚,他就得罚双份!”
“真的,这代表什么?”何慕天也问。
“问题!”杨明远说,“我满心的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复杂不堪,写木胜写,只好画问号了。”
“不成!”萧燕叫,“这不能通过!谁知道你的问号代表什么?要罚!”
“对!罚罚罚!”顿时,一片喊罚声。
“我不服气,”杨明远说,“我明明是按照心中想的画的嘛,我心里只有问号,你还让我写些什么?”
“不行,不能算,一定要罚!”胖子吴也坚持。
“我看,你还是被罚吧。”王孝城微笑地说。
杨明远迫不得已,站了起来说:
“好吧!罚就罚,罚什么?”
“唱歌!”
“跳舞!”
“京戏。”
“昆曲!”
大家乱嚷一通,结果,他唱了一支歌:
秋风起,白云飞,
草木零落雁南归……
唱得十分苍凉,又在秋风瑟瑟的黄昏里,大家都为之动容。然后他们又接着看了下去,底下是梦竹的,大家都伸长了脖子看,打开来,个个都目瞪口呆。那颗心是这样的:
大家抬起头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这颗心都有点莫测高深。小罗愣愣地说:
“真是‘有谁知’?我可看不懂!”
“我也不懂!”胖子吴说。
“大概只有画心的人自己懂!”萧燕说。
梦竹静静地坐在那儿,微微地含着笑,在众目所瞩之下,悠然地用眼光在人群中溜了一圈,她的眼睛在何慕天脸上停了几秒钟,很快地又挪开了,后者正深深地望着她,带着股探索和了然的神情。当她移开目光时,他也转开了头。小罗叫了起来:
“这总该罚了吧?比我的心还难懂!有谁能了解?梦竹!先解释!再受罚!”
梦竹抿着嘴角,浅浅地一笑,慢吞吞地说:
“真的没人看得懂?”
“没有!”小罗叫,“如果有人看得懂,就放过你这一关!你问问看有没有人能懂你的心?”
“只要有一个人懂,就不能罚我。”梦竹说。
“行!”胖子吴说,“我相信没人能了解这颗少女的心,那么复杂,又那么密密层层的,别人一个心,你怎么跑出那么多个来了?”
梦竹的眼睛又在人群中转动,似乎想找出那能了解这颗心的人。但是,半天也没人承认能了解。小罗、胖子吴、萧燕等又都闹个不停,叫着吵着要梦竹受罚。梦竹看看没有希望了,就叹了一口气,慢慢地站起身来。可是,她刚刚站起来,何慕天就咳了一声,呆呆地望着她,她也望着他,那对大眼睛似乎正脉脉地对他在做无声的询问:
“你不懂吗?你不了解吗?你不知道吗?”
何慕天调开眼光,提起一支笔来,在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微微一笑说:
“或者,这颗心的意思是如此吧!”
大家看那张纸,上面写了七个字:
重重心事有谁知?
梦竹看到了这七个字,就带着个飘忽的微笑,坐回了位子里。同时,对何慕天幽幽地看了一眼。大家看到梦竹坐了回去,知道谜底已经揭露。萧燕不服地说:
“这不是有点赖皮吗?她到底把心里的事表达了没有?”
“既然有言在先,”王孝城看了看梦竹说,“也只好饶她了!”
“我也有点不服气!”小罗说,“但是,好吧,饶就饶了她吧!算她便宜!我们还是再看看下一颗心是什么?”
下一颗是王孝城的“心”。
“解释!”小罗又大叫了起来,“这算什么东西?打哑谜吗?非好好地说明白不可!这也该罚双份!”
“我不是已经写明白了吗?”王孝城笑着说,似有意似无意地把眼光对室内溜了一圈。“有一个女孩子,在水的一方,似近非近,似远非远,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解释!”小罗仍然敲着桌子嚷,“这个‘伊人’是谁?”
“伊人吗?哈!”王孝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学着小罗的口气说,“只在此屋中,人深不知处。”
“好吧,又是一个鬼扯的!”萧燕说,“还是趁早罚他吧!”
“对!”小罗附议,“这绝不能算数。”
“梦竹那个都能算,我的还不能算?”王孝城笑着问。
“不行!非罚不可!”
“那么,我学一个老鼠叫吧!”王孝城说着,就“吱吱吱,吱吱吱”地叫了几声,然后又发出一大串的急叫,“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一直吱个不停了。
“怎么的?”萧燕问,“这只老鼠怎么了?”
“偷吃五香豆腐干,给小罗抓住尾巴了。”王孝城说。
一阵哄然大笑。接下去是萧燕的心:
大家看了,都顿时涌来无限的感慨,叹息之声纷纷而起,青春永在,欢乐长驻!行吗?这是每个人的愿望,可是,世界上没有永在的青春,也不会有长驻的欢乐!年年岁岁,常相聚首,又可能吗?这年轻的一群被炮火从各个不同的角落里,逼到这嘉陵江畔。但是,谁能知道,可以聚首多久?日月流逝,岁月倏忽,他们原是风中柳絮,水中萍草,一朝相聚,知能几时?萧燕的这颗心代表了好多人的心,大家都有点不胜感触了。萧燕看到自己的心引起了大家的伤感,就笑着把纸条一揉,说:
“乱写的!我们再看下去吧!”
底下是何慕天的,打开来,大家都围上去看,出乎意料之外地,这张纸条上面根本就没有画心,只写着几行字:
我的心早已失落,
暮色里不知飘向何方?
在座诸君有谁能寻觅?
见着了(别碰碎它)请妥为收藏!
“哈!”小罗抓了抓头,“更好了!连心都没有了!”
“别多说!罚他吧!”萧燕说。
“罚我?”何慕天问,啜了口酒,“我的心丢掉了嘛,怎么能罚我呢?心已经失落了,还怎么画得出来?”
“赖皮,调皮,加顽皮!”萧燕说,“梦竹,你认为该不该罚?”
梦竹正神思恍惚地望着那张纸条,听到萧燕问她说,她一惊,下意识地回答:“该!”
“该?”何慕天问,望着梦竹,顿时,她觉得浑身一震。梦竹那对眼睛正从纸条上移到他的脸上,眸子悄悄地转动着,静静地逡巡着,在他的脸上探索寻觅。她那小小的脸庞上醉意盎然,眼睛里盈盈地盛满了成千成万缕柔情。他全身悸动,心脏痉挛,抓起了一支筷子,他敲着酒壶说:“该!就罚我填一阕词吧。”于是他深深地望着梦竹,用低沉的嗓音,豪放而激动地念了起来:
逝水流年,人生促促,
痴情空惹闲愁!任他人嗤我,怪诞无俦,
多少幽怀暗恨,对知己畅说无休,
人静也,为抒惆怅,高啭歌喉!
难收,两行热泪,
纵大放悲声,怎散繁忧?
叹今生休矣,一任沉浮,
唯有杯杯绿醑,应怜我,别绪悠悠,
从今后,朝朝纵酒,恣意遨游!
念完,他举起酒杯,对着喉咙里灌去。许多酒泼在身上,他站起来,踉跄地走到窗前。酒在他的体内燃烧,他感到头中昏昏然,血管似乎都将迸裂。用手托住头,他凝视着窗外的月色。身后那一群人继续在玩,许多人都醉了,一部分醉于酒,一部分醉于情。喧嚣不止,吵闹不休,特宝大发酒疯,忽然高歌起“满江红”来,一部分人和在里面大唱特唱。他掉转头,一眼又看到那对眼睛,如醉如痴,如怨如慕。他迅速地再回过头去望着窗外,但是,窗外也有着那对眼睛,盈盈地飘浮在夜空的每一个角落里。他把头逃避地扑在手腕中,喃喃地问:
天哪,如果有缘,为什么相逢得这么晚?
如果没有缘,为什么又要相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