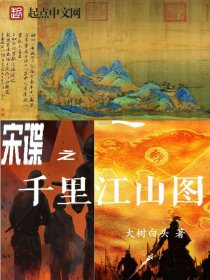第五十八章 风高放火天
军司衙门与黑水堂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
黑水堂驻在静塞监军司的分堂衙门说是作为前哨中转之用,其实,也在收集军司衙门上上下下的情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会传到兴庆府。
同时,分堂衙门的诸多差事也还需仰仗军司的支持和协助,也就不好把事情做绝,对军司的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会与以方便。
一直以来,只要宋夏边衅不起,路经静塞监军司与宋朝的秦凤路、环庆路往来的各国商贾就络绎不绝,眼见白花花的银子沉甸甸的铜钱招摇过市,一些将领自然难免眼红。
于是,军司之中便暗中兴起了走私的营生,最猖狂时,就连马匹和贵重金属等战略物资也被当作商品贩入宋境。
按照西夏的律法,走私情恶者与杀人同罪。可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身犯险者仍是层出不穷。
一则戍边的军卒甚苦,一旦起了战事,满了十六岁的男丁便要从军,年到七十方可解甲,饷银又是捉襟见肘,卖了一辈子命,最后还是老无所依。虽然走私获利的大头虽都进了长官的腰包,但军卒多多少少还是能分得一杯羹。
二来黑水堂作为专司探事情报的衙门,银两更是花得如流水一般,紧紧靠朝廷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况且有些银两使了,怕暴露了线索,也不能说出去。所以,也必须得有些“以战养战”“以情养情”的手段。
利益是最好的纽带,而走私也慢慢成了利益的代名词。几十年下来,韦州城里的军司衙门和黑水堂分堂衙门,守着静塞军司得天独厚的“通东西贯南北”的地理优势,各得所需,总体还算相安无事。
翰宗云自从任了都统以后,对于黑水堂的态度一直是敬而远之,至于黑水堂与军司中一些人搞的名堂也是佯作不知。
可是,这一切自去年起便悄然有了些变化。
黑水堂分堂衙门指挥被免,新上任的指挥权霍达则是一张黑脸,来韦州尚不到月余,便雷厉风行地查办了黑水堂涉及走私的一些将官,被诛杀流放者将近十人。
清理完自家门户之后,分堂衙门将静塞军司涉嫌走私一事捅到了兴庆府。那段时间,韦州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最终,还是多亏晋王李察哥暗中使力,将静塞军司的一位副都统诛杀,其余人才得以保全。
这件事纷纷攘攘的传言甚多。有一种说法是说,晋王府也是身陷其中,杀了副都统不过是丢车保帅而已。
翰宗云从未涉足此事,自然也是不得要领,不过,晋王府是否真的涉足此事,他却是宁信其有。这位亲家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贪财,而且是从不顾及来路。
正是缘于对晋王的了解,翰宗云觉得私下盛传的另外一个说法更是颇值得玩味,那就是彻查走私其实是濮王对晋王暗下的手段。以濮王的老道,绝不会做些有风无浪的事情,通过彻查走私牵连上晋王,倒也是讲得通
这一日,翰宗云一直忙过了三更天,才回后宅休息。刚刚出了书斋,迎面却撞见了脚步慌乱的大儿子翰德咏。
“总是这般毛毛糙糙的,成何体统?!”翰宗云轻声斥责道。
如果说起翰宗云最为引以为傲的,那绝非官爵名位,而是他的两个儿子。
长子翰德咏自幼喜好兵马,少时便随父征战军中,十八岁参加科举考试,廷试第一,被点了武状元。年少成名,人又生的标致俊朗,被晋王李察哥相中,翰德咏成了晋王府的驸马。翰德咏并不喜欢兴庆府歌舞升平的日子,一直都在静塞军司的父亲手下当差,统领着静塞军司的戍卫部队。
就在翰德咏高中武状元的那一年,八岁的二儿子翰道冲也中了童子举,翰家可谓双喜临门。
翰道冲与兄长性情迥异,不喜刀枪,最爱诗书,童子举后的十余年间,更是求学不倦,学通契丹、中原乃至西域。在以逞强好勇为能的党项贵族子弟中,翰道冲卓尔不群,独树一帜。去岁,因学名远播,被钦点入宫,做了太子李仁爱的陪读。
焦崇武被免了横山营指挥之后,翰宗云本是荐了德咏继任。料想以德咏的能为,再加上亲戚之谊,晋王也不应不允,可惜,晋王最终却是重用了李和景。
虽然翰宗云也揣度其中必是另有原委,但是也有些责怪德咏,德咏虽年长道冲十岁,却远没有弟弟沉稳,遇事总是没有静气,难免有时让人放心不下。
德咏似是一点也没理会到父亲的不悦,仍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扯着嗓门道:“父帅,黑水堂的衙门起了火,权大人没能逃出来,怕是……”
翰宗云的脑袋“嗡”的一声,披在身上的裘袍也一下子滑落到地上。
“何时起得火?”翰宗云忙问道。
“也就在半个时辰前,火势甚急,孩儿领着几百兵卒也是扑救不及……”
德咏带着哭腔说道。
一阵疾风刮过,抽打着院中树干上光秃秃的枝条,发出一阵呜咽般的啸声。
翰宗元抬眼望了一眼像块黑锅底一般的天,不由得想起一句: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或许是因为行事隐秘,黑水堂的分堂衙门没有与城中的诸多衙门挤在城中心,而是安置在韦州城东南角一座三进的小院里。
翰宗云随着德咏出了军司衙门,便望见东南方烟火升腾。
走出了两条街,离火场还很远,街面上已经都是忙着往来的军卒。
“这火烧得也是奇了,愈救却烧得越旺。”德咏嘟囔道。
翰宗云借着远处的火光,才发现儿子脸上都是黑黑的烟灰和汗水。
到了分堂衙门,只见宽阔的大门已经烧得散了架,发出瘆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一处院墙已经被推倒,担水背沙的士卒正不断从那里冲进火场。
“可知伤亡人数?”翰宗元问道。
“大致拢了一下,除了权大人之外,都逃了出来。”德咏道。
翰宗云知道权霍达只是一个人住在韦州,家眷都留在了兴庆府。
火烧了半夜,天快蒙蒙亮时方才平息,分堂衙门也已是一片废墟。
守了一夜的翰宗云急不可耐地进了火场,院中四处可见的水洼也已经结下了薄薄的一层冰。黑漆漆的残垣断壁之上,偶尔有一两只乌鸦驻足落脚,发出一两声寒彻脊骨的哀鸣。
这里,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黑水堂衙门了。
翰宗元顾不上触景伤情,他最关心的是权霍达的下落。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翰宗元让德咏带着人,与分堂衙门的人一道,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
忙活到了午时,权霍达仍然是毫无踪迹,不明下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