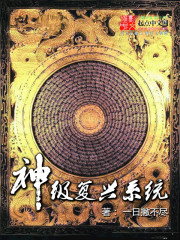第三百八十三章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
生物,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是有感情系统的,感情系统衍生虎众多适用于各个状态的情绪系统,脑容量越大的生物,衍生的情绪就会越多。
人类可能是目前上已知的生物中情绪最多的物种了。
而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有一个特征就是压抑情绪的释放,因为情绪代表着感性,完全被感性驱使跟被本能驱使是一样的,所以几千万年以来人类都在与本能和情绪作斗争。
很多管理学的书喜欢标榜一句话,叫做。
掌控了自己的情绪,就能掌控好自己的人生。
情绪千奇百种,最专业的心理学家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有一种情绪,属于人类本能,但是不属于某人经历和个体的情绪,这种情绪叫做‘共情’。
共情能力,也称移情能力,也叫神入,指的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
这种共情能力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感受也不同,看一部小说,电影会感动的落泪,代入到故事中,这是最基本的共情能力。
更深一层的不是被故事的桥段感动,而是被人物的经历感动。
最深的一层就是直接代入到人物中,通过自己的臆想加工,将当事人的悲欢离合无限扩大,几乎道分不清自己是谁的地步,这就属于严重心里疾病范围了,需要心理治疗。
之前张纯如那种共情心理是主动共情,因为被动接触和探索了太多违背人性的材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带来的压力性共情。
而现在王耀莫名其妙就哭崩了,属于无意识被动共青,没人告诉他这面旗帜的故事,光是看到这面旗帜,就好像被吸入黑洞中无法自拔,心中痛苦,挣扎,以及各种各样的极端悲观情绪让他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这已经属于共青过度,将自己完全替换到这面旗帜上面写的文字中中了。
字字含情,语重心长,不管是这面旗帜是谁送给谁的,但是送旗者在字里行间表达的悲壮和决然都是让人动容的。
世界上最戳心的事情就是生死离别,也是一个禁忌,尤其是对最爱的人,都希望对方无病无灾,长命百岁。
要经历多大的痛苦,才会送最爱的人这面死字旗,是多大的牺牲性人格,多大的悲凉,王耀此刻感同身受。
抗倭战争期间,巴渝地区一个有些偏远的小镇,当倭寇入侵的消息传来时战争局面并不乐观,镇上有一家殷实家庭,不算大富大贵,也是乡绅级别的,也姓王。
父亲王者诚早年间考取过功名算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做了点小生意,在这个小镇安家,家里有一独子,名为王建堂。
王建堂从小读书,后来在镇上从事教育工作。
倭寇入侵的消息传来后,祖国安危,民族兴亡让二十多岁的王建堂彻夜难眠,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已经到了如此为难的时刻,一夜未眠之后的王建堂决心弃笔从戎,投身道抗倭战争事业中。
他在镇上开始自发的募兵,跟几个朋友招募了一些想为国效力的年轻人,组成了一只‘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的队伍。
儿子在组建这支队伍期间的一切行为,父亲王者诚都是看在眼里的,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表态,缺钱掏钱,缺物置物。
但是战场是什么样的地方,王者诚是知道的,那是一个马革裹尸,九死一生的地方,出了家门,父子二人就可能天人永别了。
他舍得不的,但是不得不舍。
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战场,因为那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悲之事。
他不支持,是一个父亲的自私,他不反对,是一个华夏人的无私。
在儿子的队伍即将出征那一天,儿子王建堂来拜别父母,高龄老母哭的昏厥过去,家里亲戚也都默默抹泪,只有老父亲王者诚面沉如水,什么也没有交代,只是告诉儿子保重。
王建堂给父母叩头,口称不孝,父母大恩只有来世再报。
王建堂走过,王者诚独自在阴暗的书房内坐了一夜,仿佛一夜之间又老了许多,第二天一早,差人送给出征前线的儿子一个包裹。
这分包裹首先到了县长成云章的手里,他打开一看,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包裹里是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
“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
左边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本欲服役,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自觉请缨,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永往直前,勿忘本分。”
墨沉似海,字字泣血的壮烈。
很难想像得出这位白发老父是在怎样壮怀激烈的豪气下书写了这面“死”字大旗,也很难想像得出老父那只饱经沧桑的手在握住斗笔时是怎样的抖动和一挥而就或是浓墨重笔。
每一个字的起笔是如何的颤抖,收笔是多麽的悲凉。
里面都藏着一个父亲对着儿子爱和鼓励,还有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同时也吹响了战争的晚钟。
死字旗,送儿入军,送儿杀敌,送儿拭血,送儿裹尸。
从军之后的王建堂唯一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等大笑战役数十次,见证了整个抗倭战争的胜利,仙后两次获得战区长官授予的甲等功勋章、
但是战争带来荣誉并没有满足他出征时的雄心壮志,战争的残酷,敌人的残忍,一路尸山火海过来的惊恐都让他毕生难忘。
当年和他一起请缨的同乡们大多都战死沙场了。
去时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归来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那面‘死字旗’真正的被鲜血染红了,红的发黑,遗失在战场上,像是那段历史一般,被人遗失在教科书中,轻描淡写的一笔,告诉后人有这么个故事,最后我们胜利的。
但是战争的残酷和过程,也被轻描淡写的掩盖了。
抗战胜利后王建堂或者回到了家乡和父亲团聚,一直活到了1992年才去世,但是晚年这位征战沙场的民族英雄过的有些凄凉。
因为参战时是国军,也称蒋匪,见过之后虽然没有给他戴上什么帽子,但是也在当地受尽白眼,被列残党余孽无权获得工作,只是在批斗之余打零工、做苦工,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顿成泡影。
这样凄苦的生活一直到1980年,他已经六十八岁花甲高龄,因为生活凄惨被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每个月生活费十五元,结束了再上街乞讨的生活,后来修建北川文史,王建堂因为是历史的经历者,而且读书识字,被选为研究委员,参与修史。
但是那时候的物价,已经不是七十年代,二十块钱能活一个月了,年龄已经大到无法工作的老人,曾经为国捐躯马革裹尸的将军在凄苦的晚年,为了活命,多次向相关部门写信想要申请多一些的抚恤金。
当年那个在战场上无为倭寇枪林炮火的民族英雄,在晚年却跪在了他曾经拼死也要守护的土地上。
他是个战斗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忍着饥寒交迫,病死在床榻上。
何其荒唐。
临死,王建堂也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部门的回信,在饥寒中去世。
或许再等上一些日子,熬到了改革开放的日子,便不至如此凄凉了。
王建堂无嗣,从军前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从军也就丧失了。这封信和一些有关他的资料都是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军提供给樊先生。
樊先生这次带着这面仿制的‘死字旗’,希望找一些老友,多宣传宣传川军的故事,扩大战争博物馆的宣传效果。
博物馆现在并不是什么特别普遍的文化活动,但是樊先生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